● 《中国物理学》等杂志得以出版,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中国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时候仍在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 到1979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有关研究所就向美国五大国家实验室和部分大学以及西欧中心派
出了近40名学者。这些学者被称作“李政道学者”。
● 在中国政府批准了建设高能加速器的计划之后,我觉得如何建立与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合作十分重要。这种合作不能是临时的、不确定的,必须有一定的保障。
● 1986年,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NL)正在进行“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RHIC)的设计和同步辐射光源的建造,需要多种有高技术难度的加速管,就花了10多万美元向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定购了5条高水平的电子加速管。近20年后的今天,有3条仍然用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新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
□李政道
为中国高能物理尽微薄之力
高能物理是我主要的科学工作领域之一。在过去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幸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有过密切的关系,经历了它的一部分发展过程,目睹了它艰难但又成功的前进步伐。更为荣幸的是,我有可能亲身参与其间,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它一起谋求发展。现在,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正在稳步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来回顾祖国高能物理事业发展的这一段经过,我觉得或许是有意义的。
接触祖国高能物理的开始
我最早接触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是在1972年9月。自从1946年9月去美国后,那是我第一次回国访问。当我和我的夫人到了北京,在还没有见到周总理之前,周总理就请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张文裕教授先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海拔3200米的云南宇宙射线实验站,利用大型磁云室获得了一个超高能作用的事例,他们认为这一事例可能是一个新的重粒子。那时,我住在北京饭店,张文裕教授带了做具体工作的研究人员特地到北京饭店来跟我讨论,我的老朋友朱光亚也参加了讨论。参加讨论的一共大约有十来位科学家。
在这一讨论后不久,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和夫人。接见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准确地判断或然率还需要云南站的科学家们仔细复算。如果误判的或然率确实是近于百分之一,虽然不能作为新粒子发现的证据,但作为一个新现象可能的迹象,也是有价值的。我建议是否可以立即恢复中国的物理学杂志的出版,把文章用中文发表出去,加上英文的摘要。
在北京饭店讨论时,张文裕先生告诉我,他在那年年底就要去美国考察。我向周总理建议,请张先生将英文摘要带到美国去,送给美国的同行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因为不久美国费米实验室的高能质子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假使真的有这样比质子重十倍的新粒子,这完全在费米实验室加速器的能量范围内,必然会被发现。有了这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杂志上的文章和英文的摘要,中国的发现虽然仅仅是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虽然后来没有发现这种粒子,可是,《中国物理学》等杂志得以出版,也是一件好事。这同时说明,中国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时候仍在从事高能物理研究,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国自己选定发展方案
1975年,中国政府批准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特(4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这个计划叫做“七五三工程”。
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决定建造大型质子加速器,我虽然不赞成,但仍尽力去协助实现那一方案。当时我想到,要实现这个计划,困难会很多。除去经济能力和决心之外,一定要取得国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加速器实验室的帮助;同时,一定要立刻培养加速器和实验物理方面的人才。
当时,我考虑到,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NL)的AGS加速器与BPS能区较更接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于是我就与美国能源部和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联系,安排中国考察组再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访问。那时候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安排这样的访问,需要与美国政府的具体管理部门能源部打交道。在实现这一安排上,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另外,我认为,在中国加速器开始建造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培养做实验的人才。利用美国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来进行这种培养,是非常有利和有效的途径。于是在1979年1月我写信给方毅副总理,提出了《关于培养高能实验物理学者的一些建议》。在提出建议之前,我已与美国二十多所大学和三大国家高能实验室,即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NL)、费米国家实验室(FNAL)和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进行了联系。这二十多所大学都有实验组在三大实验室工作。如向它们每一个小组派一二位学者,再加上向三大高能实验室派三五位学者,总数在短期内就可达到几十位,可以满足高能加速器建成后做实验的初步要求。经我联系,上述二十几所大学和三大国家实验室都欢迎中国向它们派遣访问学者。很快中国政府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派遣学者的选拔工作。到7月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和有关研究所就向美国五大国家实验室和部分大学以及欧洲核子中心派出了近40名学者。因此,这些学者被称作“李政道学者”。
创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模式
在中国政府批准了建设高能加速器的计划之后,我觉得,如何建立与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合作十分重要。这种合作不能是临时的、不确定的,必须有一定的保障。
但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建立这种合作需要有一定的协议作为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请中国立即派一个做高能物理实际工作的考察团来美国。我征得美国能源部的同意并请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发出邀请。1979年1月,以林宗棠为首的考察团到了美国,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会议讨论和落实了美国各实验室与中国合作的具体项目,能接纳的中国访问学者及其安排。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听说邓小平、方毅要来美国访问。会后我便立即飞往华盛顿。结果,在邓小平和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和文化合作协议的同时,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这样就确定了中国要发展高能物理,要建造高能加速器,要与美国进行合作。
为了执行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我建议立即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双方派代表组成,负责整个的合作工作。经过协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于1979年6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地点是北京饭店。会议分两个小组进行:一个讨论合作项目;一个讨论专利和版权问题。据当时的估计,大家以为合作项目是容易达成一致的,而专利和版权问题则可能拖延时间甚至产生麻烦。但是,出乎预料,专利和版权方面,经过中美双方努力后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先结束了会谈。
但是一个未能预料的问题出现了。美方团长利斯表示,他来中国的时候没有授权代表能源部在中美双方协议上签字,只能以高能委员会美方主席的名义签字。中方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形成了僵局。这时已经是11日晚上了。中国的夜晚正好是美国的白天。中方坚持要美方向华盛顿请示。我和利斯团长反复商量,终于说服他向华盛顿打电话。这时已近深夜,双方代表都无意休息,等待着结果,气氛几乎近于凝滞。部分没有休息房间的中方工作人员就睡在会议室的地板上(柳怀祖和季承就是当时的工作人员)。终于,12日清晨得到了华盛顿的许可。能源部一直请示到白宫才得到批准。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和《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月中美高能物理技术合作项目》两个协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开始。这也是当时在中美高科技合作中最早的项目。
曲折的发展给予的启示
中国早在1956年就开始搞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了。16年后,1972年我第一次回祖国。据我听说和所看到的材料,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或者准确地说,高能加速器的建设,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的。国内的科学家把这一曲折过程概括为“七下八上”。
这个曲折的“七下八上”过程充分地表明,新中国在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上所走过的路是多么的不一般。在较长时间内如此反复上下地变动,显然对祖国的科技发展是不利的。追究原因,可能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一是认识方面。政治上的情形,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谈。
认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看待基础科学研究,如何处理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研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要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就必须重视基础科学;要尽早地培养年轻的基础科学人才,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应该是少而精,但必须保持这样的投资。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其他的说法,但根本的分歧之处在于,是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还是轻视它、忽视它。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它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很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基础、应用和科技开发要平衡发展,这样比较稳妥,偏激易生毛病。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而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会有鱼市场。我曾写过四句话:
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至于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研究,更是具有特殊性。由于中国经济科技水平的限制,高能物理的发展当然应该适应各方面的总体水平,进行战略性的发展。这样既能使中国很快地进入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培养出一支高科技的工作队伍,又能为今后的发展作准备,为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1986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已经展开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简称BEPC)和北京谱仪的建造工程。工程在建造过程中已经获得世界高能物理领域的科学家们的普遍认同和赞扬。自1984年BEPC动工开始,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工程进展迅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发动中国工业界,挖掘它们的巨大潜力,使它们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成品。那时,1986年,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NL)正在进行“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RHIC)的设计和同步辐射光源的建造,需要多种有高技术难度的加速管,就花了十多万美元向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定购了5条高水平的电子加速管。近20年后的今天,有三条仍然用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新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这些事实强有力地证明,基础性的高能物理研究是可以带动和推广应用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产品开发的。要祖国富强,不能忽视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必须要和应用科学、科技产品开发有平衡性的发展。
对未来的企盼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顺利建成和成功运行是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发展的良好开端。回顾中国高能物理发展这一段相当不平凡的历史,使我深有所感。1972年我第一次回祖国,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可是祖国人民能克服这困难,积极向上,努力改善,全国一心,才取得今日各方面的成就。而今日祖国高能物理的成功仅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也深觉自己的幸运,能有机会目睹祖国最近三十多年极不平凡的巨大变化。我企盼着,祖国在新的百年里、在新的时代有更好和更大的发展,祖国在物理和其他基础及应用科学的未来更有光辉的新成就! 
197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政道。他们一起谈论物理,并同意李政道培养基础人才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初,李政道夫妇初次回国,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

1984年10月,李政道陪同邓小平视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基地。

2002年,江泽民和李政道在中国美术馆观看“艺术与科学”大型展览。

2002年,朱镕基在钓鱼台接见李政道。

2002年,温家宝和李政道在中国美术馆观看“艺术与科学”大型展览。

2002年,李岚清和李政道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二十一世纪的物理学和中国的发展”研讨会上。

2001年,宋平到住处看望李政道。

1994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奠基10周年庆祝大会上,方毅和李政道亲切握手。

周光召和李政道在一起。

2004年,路甬祥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看望李政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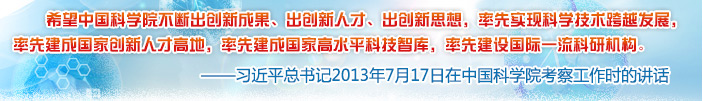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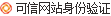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