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方
据我的朋友焦国标博士讲,北大公布改革方案以来,他们系已经开了三次讨论会。焦博士现在是副教授,如果方案施行,未来他将有两次晋升教授的机会,若不能如愿就只好离开北大了。为此焦兄正在撰写学术专著。
焦国标是著名杂文家,写过一篇《写着杂文进北大》。观点见仁见智,但焦兄的意思我明白,通过申明自己的另类身份,赞扬北大兼容并包的胸怀:有突出特长者皆有机会入教北大。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确立的传统。当年梁漱溟先生才二十多岁,学历、资历似乎都不足以服众,蔡先生经过考察,发现梁确有真才实学,遂聘他坐上印度哲学的教席。如果北大没有这个传统,恐怕焦博士是很难“写着杂文进北大”的,即使进了恐怕也不敢直说出来。
我读北大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校园里有两种评价先生的说法比较流行。一种是说,有的老先生,一辈子只写过一本小册子,然而其严谨和绵密,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都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谈论这种老先生的。还有一种说法,“是真名士自风流”,当时我记得主要是形容袁行霈、钱理群诸先生的,说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指他们为人师表的风度。例如,钱先生虽然与余杰观点分歧,但是给余杰写的那封长信,我们外人读来都很动容。立场问题毫无妥协,身为师长的那份复杂的感情却自然流露。如果想知道什么叫人文精神,不妨认真读读这封信。
至少在我毕业之前,北大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风气,真正有料的先生,是不大在乎按部就班的晋升之途的。先生的声望,主要来自学生的口碑。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边,才能够产生一辈子只写一本小册子的神话。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说的都是老黄历了。毕业十多年来,似乎北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它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气越来越罕见了,越来越变成现实生活的顺势参与者而不是质疑者,给人的感觉也越来越主流。甚至“主流”到爆出王铭铭学术丑闻来。这在过去的北大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我对母校的失望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北大对我的记忆,不过是发黄的花名策上成千上万普通名字中的一个。
不过我想,如果北大这次改革成功,大概梁漱溟是不会再有了,一辈子只写一本小册子的老先生更不会有了。“是真名士自风流”还会有吗?也许吧,但是请先出示博士证书(最好是洋博士),然后再去拼命抓住“惟二”的晋职机会。焦国标博士“写着杂文进北大”,无非也就是想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下,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写论文去吧。
我离开学校太久了,也许已经没有资格评论北大的改革。或许正如评论界普遍认为的,北大又一次在国内开创了风气,是一件大好事。我只是担心,北大将继续失去它正在失去的东西。至于失去的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或许我明明知道却不便于说出来。姑且这么说吧,至少它会失去为后来的学生所津津乐道的某些传奇。我想,为了“惟二”的机会而奋斗,对于奋斗者来说也许至关重要,但是在旁观者看来则绝无当作谈资的价值。北大的价值,很大程度在于它给了人们无穷的谈资:一个能够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一个产生很多故事和典故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当坚硬的规则在一个地方确立起来,产生典故的土壤也就硬化了。此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历史,典故最多的时候是春秋战国,越往后规则越明确越坚硬,典故反而越来越少。
也许你会说这是“必要的丧失”或“必要的代价”,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也要说,一个无法提供谈资或者典故的地方,永远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尼采一百多年前说的那句话:“理性的,太理性的”,今天我也要送给我的北大——不,我曾经的北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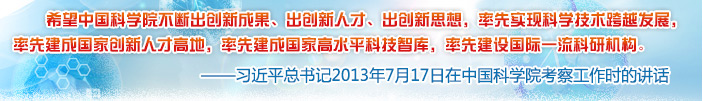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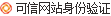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