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以龙 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12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现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副主编。
主要从事爆炸力学和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突破当时国际惯用的最大应力经验描述,建立了热塑剪切模型方程及变形局部化演变的一系列新结论,被国际一些著名实验室证明和文献引用,一些文献称其为“白模型”、“白判据”。他根据变形局部化的分析,提出延性极限的不稳定性机理,阐明了长期未能解释的变形极限图。针对真实材料受载产生大量微损伤的问题,建立了亚微秒应力脉冲技术,提出了统计细观损伤力学和演化诱致突变的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和其他科技奖3项,发表论文100多篇,英文专著2部。
1964年春,我进入中国科学院作研究生,不久就听到一种治学方法,叫做“既要会做,又要会猜”。据说,要想在科学尖端做出超越现有的新的东西,就得学会这套办法。又说,只会做不会猜,是瞎写真算,没有方向地在地上乱爬行;只会猜不会做,则会是一时聪明,最后落得一场空。当时觉得十分新鲜,仔细询问,虽然不知其源于何人何时何地,原话究竟如何,但据说是从普朗特、冯·卡门等人传下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回想长期在学校里学到的大都是如何“做”的方法,如理论方程、公式推导、计算方法、实验技能等等,针对实际问题去“做”的并不多。至于“猜”的本事,则几乎没有学过,而且一般说来,做作业和考试是不允许“猜”的。当然更不会又要猜又要做了。这也使我回想起上学时听到的两种治学方法的争论:胡适提倡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50年代被批判;于是郭沫若提议要“小心假设,大胆反证”。其实两种方法都强调了“假设”(猜)和“求证”(做)两个环节,但是在提法和分寸把握上则有不同。不久又读到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的论述,更觉得如何恰当地把握“猜”和“做”,可能是治学和研究有成与无成的一个关键。因此,我开始注意科学界,特别是力学界前辈科学家们在实际研究中是如何猜如何做的。
有一次机会,听到冯·卡门发现涡街的故事。故事是讲一位博士生研究水流中的圆柱表面的压力,测出的压力总是波动不已。这位博士生用了傻劲,将圆柱磨得滚圆,将水槽精磨固定,但是圆柱总是晃动,该生很失望。卡门终于停下来观察和思考。然后他猜想,如果水流绕过圆柱后不对称,上下两个水涡的位置就会不同。经过仔细的“做”--力学和数学分析,求解,再实验,终于发现了“卡门”涡街。这个故事成了我们研究生们经常的话题。
70年代初,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做爆炸法合成金刚石的实验,大家住在一起,白天做实验、讨论,晚上天南海北聊天,有时话题又聊回白天的实验。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较大型实验,开始除了从几篇文献和几份专利了解到的知识外,对爆炸法合成技术以及金刚石性质都知之极少。说实在的,我虽然是学爆炸力学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接触炸药,因此,虽然工作很努力,实际上却盲目性很大。起初我们照猫画虎,按文献中的示意图,简单地在碳粉上加了块覆板,就用高能炸药直接对它们加载,结果是什么也收集不回来,更不用说金刚石了。之后,重新学习了爆炸加载装置、高能炸药的性能参数,以及石墨的高压相图,这才有了工作的主动性,不久,产物能回收了,但是化验显示的却不是金刚石,那真是又累又丧气。事后也只好静下心来,从头一步步检查,根据石墨的高压相图和爆炸力学的计算,逐渐猜测到关键在于压力窗口的控制和化验分析。这个失败-学习的过程反复了许多次。有一天烧杯底部的一点点样品,终于显示出了金刚石的衍射花样。这样,我们不但做出了金刚石粉,还研制出了一种新的加载装置。
这次实践,大大增强了我的科研信心,因为我也能“猜”到和“做”出一些东西来了。但同时也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焦点问题,怎样才能猜得准。因为猜着一点,或猜得似是而非,并不太难;但真正猜得准做得对,能下科学结论,绝非易事。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后来参与郑哲敏先生领导的核爆和穿甲、破甲的流体-弹塑性模型的研究时,不断地向前辈和同事们请教,学习。懂得了要能猜准做对,必须要深入地提高自己的思维素质。
科学发展到今天,提到力学研究面前的问题,大多不再是简单的两三个量之间的关系了。这些现象往往呈现粗看似乎相悖,只有细究才能揭示其统一内在机理的特点。所以对付这类包含多个力学、物理量的复杂现象,必须恰当地交替使用显微镜和放大镜,来研究它们。
70年代末,在承担一项科研任务中,我们遇到了固体材料的一种不寻常的破坏现象。中厚的金属板材在受到子弹的高速冲击时,会在低于其强度的载荷下失效。按材料的强度设计是工业界的传统的规范做法,这个现象显然超出常规。大家讨论中提出是否应该用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断裂力学的概念来认识它。断裂力学不再将固体材料视为无缺陷的均匀体,而是考虑当均匀连续体中有了一条裂纹时,材料的承载能力会有什么变化。断裂力学成功地解决了自由轮断裂等一系列重大的工程问题,很值得借鉴。但是根据断裂力学的指标--断裂韧度去粗估,却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不一致,而且破裂断面也不像是由初始裂纹发展而来的。仔细一想,断裂力学针对的是裂纹在拉伸张开以及滑开和撕开三种模式下的破坏,而现在遇到的破坏则大多是压剪破坏,二者的受力和变形状态显然是不同的。这提醒我们不能因为想急于解决实际问题,就套一些新概念去瞎猜。
仔细观察破裂面,裂纹好像是从狭窄(微米到百微米宽)而强烈的变形带(其中的应变可以高达“一”的量级)中滋生出来,而后形成了破裂面。这时再回过头来有针对性地看文献,知道冶金和材料学家报道过的一类他们称之为“白带”的现象,而且工程师还在绝热和最大剪应力的假设下,采用了一个“绝热剪切带”发生的判据。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遇到的现象很可能是与传统的强度理论和新兴的断裂力学所描述的不同的一类破坏现象。
但是当我们试图应用工程师们的“绝热剪切带”的概念时,却发现这个概念将我们引入到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承认剪切带是“绝热”的,就意味着它的宽度是零,况且最大剪应力并不意味剪切带的存在。那么宏观的整体变形为什么会集中到狭窄的剪切带上去呢?我于是猜测,一定有一种动力驱使变形区局部化,它同时也应该就是维持剪切带宽度的耗散机制,它是“热”。沿着这条思路探索下去,揪出了一串力学和物理学变化:变形、变形硬化、应变率、应变率硬化、粘性、变形功转化为热、生温、热软化、热传导等等。简单地运用能量原理、量纲分析等,不能直接给出对这个现象的机理性的认识。经过反复摸索,综合量纲分析和数量级分析,建立了这个现象的模型和控制方程,回味出这是包含了差别很大的不同的尺度的一个问题。直观地讲,工件尺寸为厘米到米大小,而剪切带宽才若干微米,二者之比是几千以致百万倍。所以我们至少要用两把不同的尺子去描述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就是分别用肉眼和显微镜在实验中来分别观察它们的,怎么到分析机理时竟把它忘记了呢!
用这个观点往下走,发现控制整个现象的,不是简单一个无量纲量,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无量纲量:一个是反映两种耗散(粘性和热)机制之比的普朗特数,积累的数据告诉我,通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大约是一万到百万。正是这个非常大的数,决定了这个现象会同时存在两个差别很大的、物理上不同的空间尺度;另一个是反映变形的双重效应--变形硬化和热软化--的无量纲量,这个无量纲量可在变形中趋近“一”的量级。一般说来,正是这两个无量纲量的组合,决定了均匀变形必然走向不稳定性。只有在把普朗特数当成无穷大这样的一个极端情形,第二个无量纲量,才惟一地决定了“绝热剪切带”的发生。这便是工程师们设想的“绝热剪切带”,这时工程师们是从大处着眼观察问题。但是如果按材料学家的观点从小处着眼,站在剪切带里面看,上面的尺子就不对了,此处的主控因素变为向外的热耗散与向内做的功相抗衡,这决定了剪切带的结构和宽度。这样把握了这两个数,一切便变得清晰起来:均匀的剪切变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变为不稳定的;新的定态模式则是做功与传热相抗衡所决定的狭窄的剪切带。当我们后来用自己的实验,再现了这一过程,我觉得自己好像看完了一部侦探小说。小说开头的乱麻般的线索,至此就被梳理得整整齐齐了。
我们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有些事,起初似乎是猜对了,但是最终表明却是做错了。归结起来,大多数的错误常常是由于预测错了,也就是“猜”(判断)错了,近似(主要矛盾)取错了,结果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了。细想起来,这往往就是由于在运用这些简单的、经济的思维原则上出了差错。或者对现象的“质”和“量”模糊不清,或者是用错了尺子,用了大小不合适的尺子。试想,怎么能拿普通的眼镜或者望远镜看细菌呢?而看拉普拉斯这些名家,三下五除二,就猜出、做出了结果,真佩服他们的本事。
在与前辈和同事一起的不断的科研实践和学术讨论中,这些思想武装得到反复的磨炼,逐渐熟悉起来。一些上学时轻视的不肯记忆的数据,也逐渐地在头脑中扎下了根。这样才开始尝到了“会猜会做”的味道。
撰稿人:白以龙
点评:
白以龙先生对治学方法有着深入的研究,这篇“会猜会做”是他几十年思考治学的结晶;文中精选了中外科学家和他自己做学问的一些精彩例子,说明“猜”和“做”,可能是治学和研究有成与无成的一个关键。文中有生动的历史故事,有朴实的本人工作体验,有很富哲理的论述,还有对“猜”和“做”过程的细致描述,将怎样“猜”和怎样“做”作为重点,把科学方法中的假设(猜)和求证(做)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讲得透彻而深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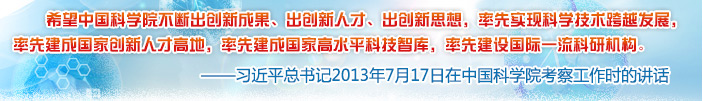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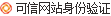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