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语教师说:“对于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出疫苗等等问题,媒体作了很多报道,我也从别的渠道听到了很多说法。但这些解答并不完全一致。这就让人心生困惑,尤其想了解导致这些判断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特别想知道相关的、基本的科学知识,但报纸对于这方面的内容介绍似乎不太够。”
对承担着科普任务的媒体而言,“在非典事件中,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令人满意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截至5月底,我国的SARS病例日增量一直维持在个位数。进入6月中旬以后,即使在疫病重灾区北京,市民出行也已很少戴口罩,人们的工作、生活已经普遍恢复正常,应该说非典事件本身已经基本结束。但作为一个涉及面极广、内涵极为丰富的灾难性突发事件,我们对它的反思正步步深入。
对承担着科普任务的媒体而言,值得反思的是:在非典事件中,我们的科普做得令人满意吗?
市民:科普文章未能满足需要
像一场梦一样的萨斯疫情离我们而去了,公众怎样看待那个时间的报纸报道?
“从4月中旬直到整个5月份,我们的生意很少,同时自己又很恐慌,于是整天趴在电视机旁看电视。对于相关节目还比较满意,感觉想知道的东西基本都知道了。”已到北京务工多年、在丰台区某招待所门口卖杂货的黄兰英说。
“我的时间很紧,较少看电视,平素喜欢读点报纸。总的说来,四月中旬以后,关于SARS的内容还是报道得比较丰富的。但也还有点不足:对于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出疫苗等等问题,媒体作了很多报道,我也从别的渠道听到了很多说法。但这些解答并不完全一致。这就让人心生困惑,尤其想了解导致这些判断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特别想知道相关的、基本的科学知识,但报纸对于这方面的内容介绍似乎不太够。”在北京清华附中分校担任英语教师的万柳稍微挑剔一点。
“不满意的地方多啦。一些媒体居然还说什么北京遭受了非典的‘突然袭击’。都出现那么久了,还‘突然’!如果不把这算成媒体的严重失职,那也至少是用语极不准确……就我所关注的报纸而言,防非典知识介绍了很多,但非典知识介绍得很少;生活知识介绍了很多,但科学知识却介绍得很少;令人困惑的应对措施介绍了很多,对于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却介绍得很少。中药凭什么可以乱吃?为什么要戴12层的口罩?干吗要不断地消毒?很少有文章解答这些问题……总的说来,相关科学知识介绍得很不系统、很不全面。”家住崇文区的离休老干部吴枝先对媒体的期望很高,失望也较多。
4~5月关于非典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涉及基本科学知识的怎么可能会比较缺乏?带着疑虑,记者仔细查阅了某大众科普报纸。
查完之后,不得不承认,在这儿,他们所抱怨的基本是事实:从4月1日至5月31日,《大众科技报》共载有大约260篇关于非典的文章,其中谈到病毒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学科基础科学知识的只有十余篇。
别的报纸情况如何呢?中国科普研究所李大光对此做了研究。据他介绍,在北京市民最恐慌、最迫切需要了解相关基础科学知识的4月份,《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晚报》等报纸也较少介绍“‘纯粹的’相关科学技术基础知识”。
和别的许多事情一样,科普也是需要时机的。在民众面临传染病威胁,如饥似渴找寻相关医学、科学基本知识的时候,正是科普的绝佳时机。为什么此时反而少有微生物学家、传染病学家、医生的科普声音见报?
科普工作者干了什么事
在SARS面前,科普工作者干了什么事呢?
赵仲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呆在家里,而是一直在外面忙。在谈非典还比较犯忌的3月份,我就帮中央十台策划了一套关于病毒、细菌等微生物的节目,并做了其中两期节目的嘉宾。4月中旬,可以比较放开地谈论非典之后,我又应《减震与抗灾》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比较大胆的文章。4月下旬,我先是被中国科协和中央文明办找去参与策划、编撰了两套挂图——一套名为《众志成城防治非典》,已经出版;另一套是宣传文明行为,也即将出版。随即,卫生部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又找到我,请我参与编撰《卫生人员防控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实用手册》。没过多久,北京科协找我为农村抗非典工作出主意。我又参与策划、制作了一套磁带——从策划、写稿到录制,只花了3天时间。然后,我又先后为福建科技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策划了10本书。非典基本控制下来之后,我又为《中国健康教育》写了一篇关于后非典时期的健康教育的论文——已经付印,马上就要发表。
当然,忙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人人为非典而担心的时候,我在科普界的同事和朋友也普遍没有躲在家里。譬如,中华医学会的那些同事就做过相关科普折页和光盘,而北京健康教育所的同行则承担了北京的部分健康热线,上海健康教育所的朋友更是把上海市的健康热线全包下来了。这段时间全国关于非典的科普书籍出了200余种,这可都是我们科普领域的同行做的啊!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也是普通人,面对新的传染病,我们也害怕,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我们确实还是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
李凤珠(北京大学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这段时间太忙了,日常生活完全被打乱。作为一个耳鼻喉科大夫,我被安排在检疫室工作,所面对的主要是从发热门诊退下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很担心。我做了大量的咨询、抚慰工作,也算是为非典科普出过一点力吧。
但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写科普文章。一则是本职工作太忙,难以抽出时间。二则觉得不大好写。似乎我所知道的人家也知道,难以写出新意来。而且在刚开始病原物没搞清楚时,也有无从下手之感。
罗明典(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我比较关心SARS病毒,但由于本职工作太忙——正在审理新版《大百科全书》微生物学方面的词条;还要为福建师范大学一本关于微生物工程的书紧急写一篇很长的序言——我没能抽出时间来写相关的科普文章。而且,即使我写了,报纸也不一定会发表啊!在几个月前我曾向有关报纸投过微生物学方面的科普稿,他们说没有这方面的版面,难以安排刊登。
报社编辑怎么说
罗教授的话引起了媒体自身的反思,文章的面世并不只关系作者,是不是该从报纸自身找原因?
相对而言,《科技日报》对有关SARS的知识介绍得较多——该报于5月13日起特意出了一个“SARS周刊”,让我们看看该报特稿部的张文天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张文天(科技日报社特稿部副主任):做SARS周刊时,我们在选题方面确实有较强的策划性,常常一做就是成系列。每个系列都可能有多个版面,上面的文章主要是由我们采写或预约的,外来自由投稿的确较难被采纳。
至于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我觉得我们还是介绍了不少,虽然按比例来说,它们比新闻报道是要少一点。也许它们确实不那么显眼,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比较零散,譬如说散见于对某个专家的采访之中。
我们比较喜欢以采访的形式做文章。因为,说老实话,有些专家的稿子并不那么好读。他们的文章有些公式化,像论文一样,比较乏味,比较难读,和普通读者不那么贴近。
而且,要写关于SARS的专门的科普文章,恐怕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一个新事物,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即使同为专家,大家的认识也并不统一。譬如说关于SARS病毒的存活期和传播渠道,直到现在大家了解得还不够确切。这种现象反映到我们的大众媒体中,就显得众说纷纭或者前后不一致——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对SARS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
当然,我们媒体的短视恐怕也是有的。它主要关注眼前的、新的东西,对于科学家50年前就已经弄清楚了的现象的确兴趣不大。它可能并不清楚,在这次的SARS事件中,那些信息也为公众所广泛关注。
科普领域中的问题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次SARS事件暴露了我国科普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
声势浩大的传染病事件从整体上讲固然很不好,但它对于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知识普及却是绝佳的时机——急需相关科学知识以抵御致命威胁的时刻也正是这些知识在人们头脑中扎根的时刻。我们的科普界和报纸传媒在抗SARS科普宣传中也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专家反应速度过慢。SARS开始肆虐北京已是时至2003年4月,距离广东的第一个病例已经5个月有余,距离广东的SARS恐慌也已2个月有余,而我们的专家仍缺乏足够的准备,不少人仍没有想好如何进行相关的科普。与此同时,专家的科普文章的通俗性、趣味性也亟待提升。
与此同时,有些报纸还是很短视的。它认为自己只是一张“新闻纸”(newspaper),不愿刊登对广大民众而言可能更有价值的“旧闻”;它认为自己只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经济实体,不愿刊登难以给自己带来当下的经济利益的文章。这恐怕是一些报纸停办科普副刊或让其缩水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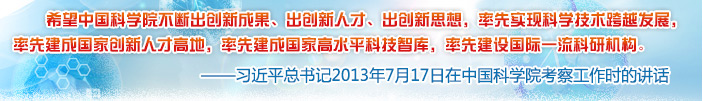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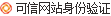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