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和深入,许多原来局部的地区性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普遍化、全球化了。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由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以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为载体、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为标志的“现代化”必将被超越,作为这种世界体系和现代化继续的“全球化”也必将被超越。
在纷繁的历史与现实当中,诸如跨国公司与WTO,卫星通讯系统与互联网,温室效应与“京都议定书”,金融危机与难民潮,核泄露、核废料转移与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活动,针锋相对的“达沃斯”与“阿雷格里”,从西雅图到罗马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甚至恐怖袭击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禽流感与SARS,以及更多的英文缩略语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AI(多边投资协定),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性的词汇,数不清的各种系列丛书、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从而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歧义百出的解说纷至沓来。细心的研究者指出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等不同流派,辨析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趋同等概念之间的差别。但也有许多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用语含混,甚至把它(以及与它有关的“现代化”)当作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ey(全球胡话)”。 例如说21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国之内所剩下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 之类,大概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
一
先来回顾一下国内学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认为“全球化”应当与“现代化”同义,所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特定时段:“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王文以“人类文明主流”为利器,回答了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什么是“理想的世界秩序”(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等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王文提出要“以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取代静态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然而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些静态的指标体系所能涵盖的。现实中一国的现代化虽然以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等为指标(这也是追赶型现代化计划发展的产物),其首要目标却是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一般是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无论通过革命还是改革)。既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大体可以用两种索取或征服来概括:一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或征服,其程度可以用一些指标体系(如生产力)来显示;二是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强国对弱国的索取或征服,迫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所造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激烈国际生存竞争甚至生死搏斗,一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败,曾经演出并且仍在上演着无数令人回肠荡气、大喜大悲的活剧。这些都是难以用指标或数字确定的动态的历史进程。王文还提出:“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这“两个取代”其实是难以并列的。从现代主权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和国际法的创立者格劳秀斯开始,国际法就被规定为防止和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纷争的一整套规则。无国家不成其为国际,而有国家则必有国家法(宪法及相关法)。 “全球化”的本义和基本特征是“超越国界”,亦即侵蚀直至消除现代化的基本载体——国家,以及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侵蚀直至最后消除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这是“全球化”对“现代化”的否定,也说明二者不仅有时段上的差别。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早已为世人所憧憬。这样的全球化用一句中国老话说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然而直到今天,这些都还只是“理想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全球化。现实当中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削弱,甚至导致达伦多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有人坚决地转向追求比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更加狭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 更不要说前苏联、前南联盟和非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带来的惨剧。
另一种看法则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把全球化看作是现实中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式,认为全球化不过是殖民-帝国主义扩张的继续。“什么是全球化?……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确切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曹文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认为它只能为政治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张目,不利于汇入人类文明主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 曹文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革命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为基础立论,立场可谓鲜明,但也有一些尚未解说清楚的地方:既然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继续,为什么不联合一切被剥削被控制者予以反对?面对“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某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不许它在一些地方造成诸如加强剥削、损害生态和人性、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后果,同时却默许它在另一些地方继续制造这样的后果,如果民族主义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那又如何解释某一个或一些群体“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正当性?一句话,如何利用将会造成上述直接后果的全球化来实现发展中的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在已经写了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笔下,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实是同义语。约瑟夫•奈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里则使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年间的全球化”等概念,并这样写道:
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
来自美国农业大省北卡罗莱纳的考克莱尼斯教授也认为:全球化迄今也还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当时,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使得全世界的农业联系更紧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16-17%;此外,19世纪末列强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军事基地,强权进入全球性争夺。
鉴于上述事实,乔姆斯基的以下总结应当被认为是可信的:“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多么‘全球化’。” 这些史实和关于它们的论述,或许还都可以用来佐证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甚至本来就是同一过程。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在大英帝国一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化/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就已经遭遇强有力挑战。美国学者司马万以实例说明了当时自由贸易对德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威胁如何助长了容克地主的政治影响。 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英国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挑战,结果不仅使英国人从对其“世界工厂”的辉煌业绩和维多利亚盛世的陶醉中惊醒,不仅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这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终止,而且是规模同样空前的世界范围的“30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身陷其中的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二
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在几百年间充斥着国家之间流血和不流血的冲突,继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总是要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挑战既有的霸权。这些在历史记录上都应当是没有异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框架里被表述为和平与战争、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国家兴衰与霸权的周期性更替。金德尔伯格等则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表述了这种不平衡性:领先国家在某个时间被他国在“赶超”过程中赶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考虑的是世界经济是否必然逐渐形成等级结构,是“国家生命力”的类似个人生死的周期,而不是谁现在位居“第一”。 霸权是如何更替的,为什么一些挑战者成功而另一些挑战者失败——这些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要提出的是,在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际体系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在仍然由“丛林法则”支配的大国、强国激烈争夺之下,看不到出现“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希望。如果非要把强国对弱国、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民众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全球性的霸权、对峙、战争等等也说成是一种全球化,那只能是霸权和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imperialism),即帝国主义从地方性势力演化成世界帝国,演化成对整个世界的统治。16世纪以后400多年间的世界历史大体如此。
1997年,针对美国国内民主的衰退和主张由美国主导世界的“新秩序”说,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茨•舒尔曼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要人们警惕美国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和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更早些时候,还在两霸激烈对抗的1974年,他就著书提出:世界正在走向一种由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中心所控制的全球秩序。 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两霸对抗结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状和未来持乐观态度者开始高扬普遍主义和“历史终结”论,以经济、文化和学术的全球化为当今世界顺之者昌、拒之者亡的大趋势。悲观者、保守派则大讲“文明的冲突”,甚至认为今日人类已经进入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告终,但它并未如人所预料的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或许进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更为危险的时代。 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扩大,为了平衡既有的纯粹归结为资本与商品流动的失衡的全球化,如何建立全球性伦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全球行为规范问题也受到普遍关注。 这又引起对全球性伦理的多样解释。例如,从“软权力”角度研究全球化新秩序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名家约瑟夫•奈就认为:“软权力”由控制全球信息流动的社会所控制,其他社会则都要采用该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行为规范。
不管是“软权力”还是硬权力,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看来都得承认:作为历史与现实进程的全球化,跟一个控制全球秩序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中心”关系密切。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心:是理想的“全球共同体主权”?还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大国强权?上述弗兰茨•舒尔曼的演讲还反复谈到:2500年以来由大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这暗示某些新兴帝国可以延续并成为长久的世界秩序——世界王国(world realm),用中文表示即“天下”。这些话和前引“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说 , 使笔者不由地想起了一段关于中国从战国时代列强并立到秦灭六国混一天下的野史。场面宏大的中国影片《英雄》,讲了两个胸怀亡国破家之恨的赵国剑客从千方百计刺杀秦王到主动放弃刺秦、最后双双舍生取义的故事(秦王不因其放弃暗杀活动而赦免他们,同伴也不会原谅他们)。放弃的原因不是仇恨消解,而是他们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粹——书法当中直接或间接地悟出了剑术的最高境界——“心中无剑”和“不杀”的道理,此外还有明显地是秦人的后代强加于两千年前的两个普通复仇者的“天下”观念。这当然不是信史,但不妨当作一个耐人寻味的隐喻:一统天下其实是可以有不同方式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文化”,攻城略地杀人如麻以求造成“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琅琊台刻石)是“武化”。这“两化”其实在当代世界一直并行也一直冲突着。如果说古时还没有天下大同和平达成的条件,古人还不懂人类社会平等合作和平发展的道理,积两千年的智慧、理性和数百年(特别是近百年)大规模战争造成巨大破坏伤亡的惨痛教训,人类还能让以武力和霸权凌驾于一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吗?“春秋无义战”。当今的罗马帝国和某些依附于帝国的国家所发动的难道都是“正义之战”?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难道不是美国介入中东的首要战略目标?连年的巴以流血冲突中以色列的强霸作为,不是连美国也时有批评吗?
说白了,今天的全球化也存在着不同路径的对立和冲突,存在“两种全球化”之争。在两个对立阵营与两个平行市场早已结束、现代世界体系无孔不入、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回到跟世界经济与政治隔绝的状态。但全球化如何“化”,由谁来“化”,仍旧是一个一切关心人类和地球未来的人们都应深长思之的问题。
三
有人形象地描绘了“全球化的颠峰状态”:前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因司机醉酒而亡于车祸。司机是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他们到一条法国隧道里。车祸发生以后,抢救者是美国医生,用的药则来自巴西! 由于现实中“国族认同”(nationalism)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还没有被另一个仍处于想象中的全球共同体认同所取代,许多人心目中的全球化还只限于经济领域,因而以各种方式强调“经济全球化”。 但“全球化大叙事”的全部内容显然不是全球经济或者世界市场所能涵盖的,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和面向全球化的各国首脑高峰会议议程,也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即使仅以经济论,实际进程中的由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众多亚非拉国家当下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亚洲内陆和海岛的许多地界正在恐怖与反恐怖的战火中颤抖,经济情形不说也罢。仅以非洲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压力下,大部分非洲国家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依照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结构调整”的改革方案,走上了市场化和全球化之路。由于背离国情,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在此形势下,60年代已经走向低潮的、强调恢复“自信”、“自强”的泛非主义重新兴起。 笔者曾于1996年9月赴桑给巴尔参加“南-南发展历史研究交流项目(SEPHIS)”年会并顺访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展研究院,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结构调整”方案的负面评价、对政府官员、跨国公司乃至提供调整方案和贷款的世界银行、IMF的批评。年会上的一些发言则很像车祸发生以后人们对醉酒司机和“狗仔”追踪者的训斥,还包括对无力回天的医生和所用药物的指责。借用《帝国》的一个隐喻,“正是药品本身威胁到病人的生命。”
联合国在1974年就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要求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以保证持续的稳步加速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随后,一个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领导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在比较了全球巨额军费开支和少得可怜的发展援助、列举了遍布世界的贫困和饥饿以及环境灾难、恐怖主义之后,呼吁正视“危险和挑战——战争、胡乱、自我毁灭——的全球化”,正视“毁灭还是发展”这一紧迫的人类前景问题。 但根据联合国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分别占世界人口1/5的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的人均GNP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0的60:1,1997年进一步扩大到74:1;而这几十年正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 将这类言辞借用于今日世界,不是太平盛世学者优游偃仰之余故做的“危言”,而是对现实人类生存状况和危机的至为贴近的描述。斯蒂芬•克莱斯勒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中,以墨西哥为个案分析了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困境和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状况和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很脆弱。市场导向的制度虽能给它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全球经济的波动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内政治稳定。 乔姆斯基也以墨西哥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华盛顿共识实验失败的最新例证。这个国家曾被视为他国应当学习的榜样,而今却有一半人食不果腹。1994年元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同一天,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印地安农民揭竿而起。《协定》被起义者称为是“给印地安人判了死刑”。起义者的要求具体而明确:“为了争取工作、耕地、住宅、食品、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平和和平”。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比墨西哥更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由魏地拉政变(1976)开始的7年是面向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阿根廷盛行的时期,其“成果”却是对阿根廷财富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开放商品市场,造成许多民族企业破产;开放资本市场,纵容了国际金融资本在阿根廷的猖狂投机活动。1983年恢复民主制度,经过几次“正统的”、即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之后,经济形势再次失控,资本加紧外逃,国际金融机构又见死不救,以致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国内局势空前混乱。1989年正义党梅内姆政府上台执政,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提出了一套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由于“世界生产体系全球化阶段的内在逻辑是非调控和向世界贸易开放的持续不断的进程”,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战略已经行不通。为了“适应以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和经济体系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现实”,梅内姆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放弃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按比较优势原则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以此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果却是:曾在20世纪初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6位、人均GDP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80%的阿根廷,在一个世纪后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 797美元几乎减少一半;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阿根廷不但不像世界银行几年前曾经预言的那样是“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且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仅仅好过拉美5个最穷国。
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常常有人祭起“贸易自由主义”的旗帜,攻击“贸易保护主义”。且不说“贸易自由”作为一种“主义”的普世价值几何(恩格斯就曾指认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惟一大工业中心这种假设上的” ),如果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现实中,其实很难找到纯然的两种“主义”者——向往自由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受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威胁的领域,不得不实行或者要求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而高唱“贸易自由”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发达国家,也常常对自己的某些部门高筑壁垒。日美之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法国农民将拖拉机停在高速公路上示威反对削减农业补贴,所争的都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各自在国际贸易中的现实利益。无数事实证明,那种只要求别人遵行的贸易自由“主义”,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强大的金融业为武器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迄无明显成果。支配整个世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乔姆斯基和他的朋友称之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事实世界政府”的核心)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的一系列理论,一种背弃古典自由主义的起码的“结果平等”要求、如不加以限制将会导致永远的状况不平等和民主终结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 遵循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所有经济体(特别是所有发展中的经济体)都应当向整个世界(可以读做“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允许资金、商品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仅看今日世界市场的区域性分割,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狼烟四起的关税战、贸易战,就可知道这些在眼下还做不到。其中,一种必要然而特殊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全球自由流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自由流动,其实现更是遥遥无期。即使“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也势必超出经济范畴,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而在由发达国家指定规则和基本上由发达国家国界所限制的劳动力要素非自由流动条件下,理论上的“贸易自由主义”是很容易演变成为实际上的“贸易帝国主义”甚至“经济霸权主义”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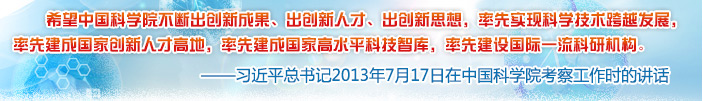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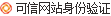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