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到8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官方的新闻稿及大多数与会中国数学家的口中,被形容为“21世纪的首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7年,但1900年8月6日却是大会真正确立起自己世界数学界最重要会议地位的起始。这一天,38岁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走上讲台,以“揭开隐藏在未来中的面纱,探索未来世纪的发展前景,谁不高兴呢?”作为开始,提出了23个他认为全世界数学家在新世纪中应当关注和解决的重要数学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人所熟知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当这位大师在1943年的情人节去世时,德国《自然》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上很难有一位数学家的努力不是以某种途径源于希尔伯特的工作。而哥廷根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卡拉西奥多里则在唁电中写道:“你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你教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这是一种略微夸张的说法,但无可辩驳的是,在迄今为止获得菲尔茨奖的学者中,有半数以上人的工作与希尔伯特问题有关。
102年过去,但当我们把举办在自己国家里的这次数学大会比喻为另一次具有世纪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由始至终却都透着一份中气不足的感觉。
8月20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英文演讲中尴尬地用中文给来自各国的数学家解释孔夫子的“仁”,大会主席吴文俊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贡献和丝绸之路,北京市市长刘琪则告诉大家,数学在北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朱世杰。
真要为某一次会议赋予世纪性意义,一双具开创性的、能够看得清未来方向的眼睛应该是最重要的。而在我们的这次大会上,这双眼睛似乎是缺席了。
辉煌还是式微?
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帕利斯在评价此次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时候,用了两个“第一”: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出席开幕式并为菲尔茨奖得主颁奖,这是历史上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
曾经参加过1990、1994、1998年三次大会的一位数学家对这两点感触颇深。他对记者说,在国外举行的数学家大会,几乎在举办地掀不起什么波澜,开幕式最多也就有个市长来发发言,从未出现过国家主席、副总理共同出席的场面。他指着自己代表证上的编号告诉记者,1897年第一届数学家大会的代表只有200名,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代表人数增加到2000多人,此后大多在3000到4000人之间浮动。然而据粗略统计,本次大会的参加人数,应当在6200人以上。
曾参加过1950年美国坎布里奇(Cambridge)数学家大会的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在自传中写道:“坎布里奇大会几乎已经过大,后来的各次大会已非‘几乎’而肯定是过大。”他建议,如果与会者看到某位自己想要与之交谈的人,最好当时就逮住他——否则再偶尔碰见他的机会是零。
在会场上,记者曾经邂逅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菲利普·格利菲斯先生。应记者请求,格利菲斯教授刚要向记者介绍有关数学联盟和数学家大会情况,就被一位组委会成员因事叫走。格利菲斯教授很礼貌地向记者表示回头再谈,只要等几分钟——但结果是,在那之后,记者再也没能找到这位数学家。不用万人,6000人已经是足够大的数字。
规格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是否让数学家大会发挥的学科影响力也同样增强呢?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数学家都这样认为。现在加拿大某公司任职的赵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曾师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1998年菲尔茨特别奖得主怀尔斯。他对记者指出,数学家大会目前的意义更多在于展示,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
如果追溯数学家大会历史,不难看出,在它创立早期,一方面时代要求数学从孤立研究走向广泛交流;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渠道不畅也的确成为不同国家间数学家研究协作和成果分享的屏障。因此,一个定期的、世界性数学家集会的确对数学发展有莫大的推动力。
然而,当网络时代来临,地理屏障渐渐被打破,虽然交流和协作越来越成为必须,但一个会议所能起到的作用却日益微小。与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不但不能促进交流,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仁教授是本次数学家大会组合论卫星会议的主办者之一。他向记者指出,在数学家大会上,听听1小时大会报告和45分钟邀请报告对听众而言,只是保持学术敏感性的一个途径。不但深入了解谈不上,由于学科的不同分支,可能连听懂都很困难。而对于作报告者,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已有成就的肯定,是荣誉的象征。更深入的专业问题讨论,往往要通过其他途径——如老朋友间的通信、会面、小规模的专业学术会议等——来实现。
数学的中国口音
不管就数学家大会本身意义的讨论结果为何,无可置疑的是,此次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对于中国数学界的意义是深远的。此次大会是“作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的华人数学家人数最多的一届数学家大会”。作1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数学家共计3位,作45分钟邀请报告的人数更多达21位。“或许有折扣,但不多。实力还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各学科研究中,数学是在国际上地位最高、华人力量最强的学科之一。”吴文俊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然而,在这一片中国口音的英语中,你依然不难听出另一种尴尬。虽然同是华人,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学者却只有11人,其他均为华裔外国人,或是在国外留学已经获得了绿卡或外国国籍的数学家。而即使是那11位大陆学者,也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对这种情况,袁亚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我们都知道华罗庚是大师,陈景润的成就同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一个华罗庚难,但出陈景润更难。”袁亚湘的意思是,真正由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实在太少了。目前数得出来的几位华裔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和丘成桐是美国人,吴文俊是法国留学生,田刚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就连袁亚湘自己,也是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
数学从不拒绝个人魅力
霍金来了。
纳什也来了。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名字远比数学家大会更有魅力也更为熟悉。一个例子是,在某大新闻网站关于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专题页面上,与这两个人相关的新闻占到2/3,而拜那部奥斯卡获奖电影之赐,众多数学家也纷纷“美丽”起来。
有一篇评论把这归结为数学家的个人魅力,记者并不这么认为。霍金是物理学家,纳什虽是正儿八经普林斯顿出来的大数学家,但为他带来最大声誉的,却是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之所以会成为科学明星,都同电影这一介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朗-霍华德导演的《美丽心灵》之于纳什,犹如埃洛尔·莫雷斯导演的《时间简史》之于霍金。
一种观点是这两个人的名声远超出自身的学术成就,而本次数学家大会借邀请这两人作公众报告的机会成功炒作了自己。持此种看法的人中不乏来自普林斯顿或剑桥牛津的与会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担任本次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的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袁亚湘指出,邀请声誉较高的科学家(不限于数学家)作公众报告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传统之一,挑选作报告学者的标准,也主要从其学术成及公众认知度着眼,目的只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对数学的更广泛兴趣。
袁亚湘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较少功利性的活动。他举例说,本次大会邀请作公众报告的学者共有4位,在霍金与纳什之外,还有纽约大学的一名数学教育家和中国的吴文俊。“如果真的是为了炒作,我们完全可以请到名气足以和霍金、纳什并列的科学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于公众对这两位科学家的格外关注,袁亚湘用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作为评价——“数学从不拒绝个人魅力”。
菲尔茨奖的故事
本届菲尔茨奖的两位得主是法国数学家洛朗·拉佛阁和俄罗斯裔数学家弗拉基米尔·沃沃斯基。菲尔茨奖的创办者约翰·查尔斯·菲尔茨曾明确表示,他不愿该奖的名称与“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的名字相联系”。
即使今年美国股市的恶劣表现使诺贝尔奖金总额大幅缩水,但每项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仍有望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0万美元)。同财大气粗的诺贝尔奖相比,菲尔茨奖显得未免有些寒酸: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得到的奖金被如何使用时,沃沃斯基说,可以用它去度假,虽然可能1500美元还不太够。不过,菲尔茨奖与诺贝尔奖的差别绝不仅在于奖金多少。
数学界中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言,说是诺贝尔与当时瑞典著名数学家米塔格-莱夫勒(Mittag-Leffler)因为争夺某一女子而失和,为防止莱夫勒获取自己设立的奖项,诺贝尔故意将被誉为“科学的皇后”的数学排斥于诺贝尔奖之外。据说与莱夫勒保有“持久的友谊”的菲尔茨设立“菲尔茨奖”的一部分意图就是为好友伸张正义,为数学家设立一个与诺贝尔奖对立的奖。
关于菲尔茨奖和诺贝尔奖的另一个有趣比较是在年龄方面。虽然纳什绝对是此次国际数学家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但作为数学家,他从未获过菲尔茨奖。从1936年设立之日起,菲尔茨奖对于获奖者的要求中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得主年龄不超过40岁。而尽管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年龄从未作过规定,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年龄在40岁以下。因此,数学界又流传着另一种说法:你是一个很想获大奖的年轻数学家吗?如果到了40岁还没有拿到菲尔茨奖,不如转行学经济学,争取拿诺贝尔奖吧!
当然,40岁以上的数学家也大可不必绝望。1978年设立的Wolf基金就是另一条出路——虽然获得Wolf数学奖的难度可能更在菲尔茨奖之上。1984年,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菲尔茨奖的华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的丘成桐的指导教授陈省身与当代最富传奇色彩的数学家保罗·俄尔多斯(Paul Erdos)同获Wolf数学奖。这是国际数学界与中国人有关的少有的佳话之一。
大师效应与数学的全球化—专访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秘书长袁亚湘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其他重要学科的国际会议都是按学科命名的,比如国际物理大会、国际化学大会,而不叫国际物理学家大会或国际化学家大会。联系到本次会议前期各方面对霍金和纳什的追捧,您觉得这是否也是一种数学的明星效应呢?
袁亚湘:数学家大会为什么不叫数学大会的问题,可能涉及到许多历史上的原因,我无从查考。但就我个人感觉,首先数学更强调个人作用,更强调人本身。像武侠小说一样,一个高手,比如说华罗庚,他本身就代表一个学派,而像物理或化学可能更强调学科间的配合与协作。从各国来看,数学家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比较大。德国、法国都有数学家担任总统咨询顾问的传统。拿中国来说,虽然数学家在科学家中占比例比较小,但华罗庚、冯康、陈景润、吴文俊、杨乐都是数学家。数学家个人的知名度比较容易高,这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华罗庚这样的大师了,而公众对数学的热情也远不如当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呢?
袁亚湘:从单个人来看,像华罗庚这样的大师现在中国的确没有。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来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时势造英雄。比如英国,现在也没有出过牛顿这样的大师。霍金被称为“活着的爱因斯坦”,实际上说的还是爱因斯坦要更伟大一些。这种攀比是我不太看重的。至于公众热情降低,数学家知名度下降,同时代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现在人们的选择和兴趣都比从前的时代更丰富了,不像我们这一代人,会受一篇文章一个报道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应该说中国的数学水平是提高了。这次大会有24名华人学者作报告,这很说明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会议宣传材料反复提到1900年巴黎数学家大会的“希尔伯特23个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这23个问题毫无疑问极大影响了数学界的研究方向。但也有一个疑问是,借助数学家大会的影响力成为主流的这23个问题不可能涵盖数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那么会不会整个数学界的资源都流向这23个问题,从而导致一些非主流的问题被忽视?
袁亚湘:这种事情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但也并不完全如此。我的观点是,真正重要的数学观点是不可能被压制的。希尔伯特提出的问题,由于他本身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上,对未来的方向看得比较清,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问题。但不是说他不说,别人就不会做了。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大会被描述为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数学家大会。您在前面也提到了全球化问题。那么,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可以充分调动数学学科资源的权威会议,您觉得是否有助于消除数学界的地缘差异?
袁亚湘:这种数学研究上的地缘差异是一直存在的,它很大程度上同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数学家大会以往在弥补这种差异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第三世界国家数学家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较少,但近来则有所改善。比如,我在1990年参加日本数学家大会时,大会就为像我这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供了资助。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供21万美元的资助,使他们有同世界级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互联网和交通的日益方便都使交流越来越频繁,真正高水平的科学家一样可以得到展示自己成就的机会。学派之间的差别当然还会存在,但不再是负面的了。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非线性最优化问题。曾获首届青年国际数值分析奖、冯康科学计算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数学中国与数学家—专访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吴文俊
中国是否数学强国?
邵滨鸿: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时候往往会举办奥运会,一方面说明了该国国力强盛,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奥运会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举办被称为“数学的奥运会”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否说明中国现在在国际上是一个数学强国?
吴文俊:怎样的强不好说,但反正有一定地位。这一次大会,作报告人数最多的当然是美国;第二位是以色列,可能其中包括许多犹太人;第三位就是中国,超过了日本、英国和法国。这是我没有预计到的。
邵滨鸿:能不能从这个作报告人数排名第三的情况,得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数学强国的结论?
吴文俊: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排名要打点折扣,还是不要自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会起到反作用。邵滨鸿:那么依您个人的标准,说到中国整体数学水平提高,成为世界数学强国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呢?
吴文俊:如果以创新的标准来看,比如某一个方向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外国人跟着我们来做。这么看来,我觉得就还不太够,因为目前很难说有哪些数学方向是我们提出来的。
数学家的话语权
邵滨鸿: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数学地位,我们又是如何争取到主办本次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呢?
吴文俊:争取到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主要是因为国外数学界同中国留学人才接触比较多,了解你数学上的成绩。像上一届的数学家大会主席就提过,他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年轻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潜力,所以非常赞成在中国举行大会。当然外交活动可以起一些作用,但许多事不是靠外交游说就能做到的。
邵滨鸿:作为大会主席,你会在大会上作报告吗?内容是什么?
吴文俊:我没有资格在大会上作报告。大会学术报告评选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邵滨鸿:你为什么在面对全世界数学家的大会上去跟人家讲数学是做什么的?你觉得他们不是很清楚吗?
吴文俊:我查到过许多关于数学意义的说法,各种各样错综复杂,都是名家的话。可能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都有不同方式的话,我就讲我要说的话,我不能照顾别的。我还要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我个人完全赞成恩格斯的话,我想你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都这么讲,没有关系。
邵滨鸿:是不是因为您是大会主席,您有话语权?
吴文俊:是。不过我要想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来讲,太武断不行。我要照顾大局,不能光凭我一个人说了算。
作为国家的数学家
邵滨鸿:2001年您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奖,江泽民主席给您颁奖,跟您说了什么话吗?
吴文俊: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祝贺我,都是经过排练的。江主席从这边走过来,我从那边走过去,握握手,他祝贺我一下,然后把奖品拿给我,拍一张照,我退下来——就是这样子。
邵滨鸿:您个人怎么看待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布一个奖?
吴文俊:就是说明国家对一个奖的重视,通过一件具体事情提高各方面重视。
邵滨鸿:作为一个数学家,您是否觉得数学家中古怪的人比较多?在中国,数学家和数学是否被神话了?
吴文俊:我不觉得数学家古里古怪,学院里面看不出哪个数学家特别古怪。陈景润是比较特殊的,但我觉得他很正常,我能理解他的思想。我想数学家的古怪是被夸大了的。中国把数学和数学家神话的风气也特别盛,好像数学神秘得不得了,数学家一定是怎么一个样子,这是中国特有的。
邵滨鸿:以您为例,我听说您无论碰到什么事情,观察什么,都会把它和您研究的数学联系在一起,是吗?
吴文俊:这不是事实。有些联系是自然的,有时拉不上也不能硬拉。比如我喜欢看别人下围棋,非说我成心在里面抓数学,那就是神经病了。
(吴文俊:中国科学院院士。以拓扑学方面的“吴文俊公式”和数学机械化方面的“吴文俊方法”闻名于世。于1956年与钱学森和华罗庚一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7年38岁时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2001年中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摘自新浪科技 记者鲁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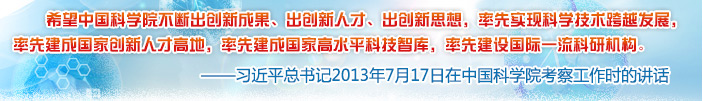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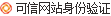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