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学 古植物学和地层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7年4月生于湖南郴县。1942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兼古植物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地质古生物学工作。古植物学研究上的代表作《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中许多属种被收入了国内外多种古植物学教科书或论丛,对华北石炭、二叠系划分提出的新观点和建立的植物组合顺序,至今仍在华北煤田地质勘探中广泛应用;作为生物地层学研究领域重要成果的《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对不少传统观念作了重要订正并补充了新资料;对一些有特别意义的植物化石、含煤地层和植物地理划区,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已发表论文和专著有140多篇(本),并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院、部、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
中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借用诸家诗词来表达他治学的三种境界。其中第三句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对自然科学家们追求真理或创新而言,也是至理名言。首先是“众里”,一是面对前人的已有成果即文献,也许洋洋大观,甚至汗牛充栋,需要全面或详或略的大体了解,尤其对众说纷纭的问题,得摸清各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对搞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人而言,这个“众里”,就是多作野外地质考察、采集尽可能多的化石标本。总之,就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任何科研创新的前提。说到“寻”,即寻求某个问题的解决、概念的创新乃至大的发现或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坚忍不拔的刻苦努力,千百度地寻寻觅觅,才会有“却在灯火阑珊处”那豁然开朗的成功喜悦。当然,“寻”,还有个思想方法的指导问题。依我的体会,懂点哲学,对搞科研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少走弯路。自然界的现象如同万花筒,但要找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事物的本质,却非常不容易,要尽可能避免形而上学、简单化甚至歪曲的三段论,学会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综合分析的辩证思维,特别是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作为一个年届耄耋的地层古植物学家,我在这个领域里耕耘六十余年了,事业上略有小成,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以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创造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以及许多同行,包括老师前辈的教诲鼓励和朋友学生的大力帮助。前面解题的一段话,也是我的经验之谈。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略加阐述,我是如何求索的。
由表及里,综合分析
《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一书,涉及中外文献、专著约500种,从泥盆系至二叠系的每个地层单元,几乎都是众说纷纭,包括这些地层的命名沿革、定义、分布范围、上下接触关系、化石内涵、时代归属、对比关系等等,我都一一加以考证,与我长期野外地质调查相结合,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综合分析,既尊重先人的劳动成果,又不迷信权威甚至自己的老师,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例如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地层单元五通组(曾误称“乌桐组”、“梧桐组”),仅时代问题,意见分歧就很大。当时古植物学家定其时代为早石炭世,而鱼类化石专家根据更古老的胴甲鱼类的发现,认为属中泥盆世晚期-晚泥盆世早期,二者相差两千多万年。我根据对植物群的综合分析,并查阅有关鱼类化石文献,特别是注意到近代非洲东海岸深海还发现了数量极少的茅尾鱼(空棘鱼类残存的一种,被称之为主要生存于泥盆纪总鳍类的“活化石”)的事实,从而推论其时代为晚泥盆世,这个结论至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古生物学,不同于精密科学如数理化,是从经验、描述发展起来的学科,往往使用归纳法,例如“以往,某类(或属种)化石都是发现于某时代的,现在我发现的也是这类化石,所以也是某时代的”,这个三段论的推理,很明显,是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定的,因为大前提中有“以住”的限制,也就是说,大前提不准确,所以据此推出来的结论未必是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
关于华北“G层铝土矿”或“山西式”铁矿的时代和对比问题,由于牵涉的文献和争论很多,这里不能详述。简言之,广泛分布于华北奥陶纪灰岩之上的这两种沉积,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层位很稳定,二者可以作为独立地层单元名词使用,且代表不同的时代,“G层铝土矿”为早石炭世,与华南的某些铝土矿可以对比,“山西式”铁矿最可能属晚泥盆世,与华南的“宁乡式”铁相当,当时“古气候的一致性”是这种对比的出发点。然而华北和华南这两个不同的地质板块,无论所处纬度及大地构造发展史都是不同的,单用所谓“气候的一致性”来对比地层,是不科学的。根据我自己的野外观察,并结合某些专家的合理解释和建议,我总结了这两种沉积的命名和认识沿革、地质地理分布情况,并得出了为各家公认的几条结论:(1)这二者虽有上下关系,但无论从地球化学的亲缘看,或从层位的水平追踪来看,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决不能截然划分为两个地层单位,更不能作为正式的地层单元;(2)“G层铝土矿”与上覆地层基本上是整合的,何况,自上而下铝土矿有七层,故其时代应以上覆岩层的时代为准,大多数为中石炭世,少数是晚石炭世,甚至二叠纪;(3)即使同为“G层铝土矿”,因与各地海水进退有因果关系,也有同一时代不同时段的差别。
内外结合,博采众长
关于华夏植物群及其相关地层的时代和对比问题。由于欧洲是古植物学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科学史,也出过不少的古植物学大家,部分受“欧洲即世界”的影响,反映到古植物学的研究上,就很容易把在欧洲一隅所得的归纳性结论推广到其他国家,这种片面性即使在某些优秀的古植物学家的著作中也在所难免,并且影响到我国的学者。例如著名的瑞典古植物学家赫勒,他所著的《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1927),至今仍不失为一部经典,但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认识有一个过程,他对相关植物群的解释和地层时代的确定,就不无缺点甚至错误。如山西组、上石盒子组或龙潭组、“石千峰组”的时代、对比问题,对华夏植物群与前苏联的安加拉植物群的关系问题等,他的结论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我在《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涉及中外文献、专著近300种)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丰富的植物化石材料,不但大大充实了赫勒早年奠定基础的太原组、山西组植物群组合内容,并根据当时已发表的大量资料,较全面地总结了全国石炭纪-二叠纪植物组合的特点、演替概况以及其中某些代表属种的消长关系,对我国此期陆相或海陆交互相地层的划分、对比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结合相关地层、古生物(包括古动物)、古地理、古气候、沉积学等领域研究的新进展,我对前述赫勒教授等人的观点,本来早就有怀疑,逐一进行多方位的分析、深入的讨论,从而得出了与之不同的新结论,40年过去了,我的那些观点,虽然很难说是完全正确,但大多基本上站稳了脚跟。我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太原组到山西组以及上石盒子组或龙潭组,赫勒等人定的时代都偏老,从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对我国石炭-二叠纪植物群的生态和古环境的特殊性重视不够,而过分注意某些欧美植物成分的时代价值。例如在欧洲,温暖湿润的成煤沼泽植物生态体系主要在石炭纪,到早二叠世早期反映干旱气候的红色地层已广泛出现,石炭纪许多植物已不复存在,而在我国,二叠纪早、中期仍是成煤环境,到华南龙潭组仍然如此,晚二叠世在华北才出现典型的红层,在华南却在晚二叠世晚期仍有煤组出现,所以许多欧美石炭纪色彩的植物在我国特别有利的生态条件下,有较长的地质历程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华夏植物群中有许多特有的分子,它们在植物群中的比例,包括时代较新色彩成分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太原组,我当时虽追随地质古生物(包括古动物)学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定为晚石炭世,但我也指出,将其放在晚石炭世“是为许多外国地质学家所不赞同的”,现在,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是,太原组的大部分已划归早二叠世。山西组的时代,由于当时所知植物化石很少和性质不明,而地层岩性和含煤情况又与太原组相近,赫勒原定为石炭-二叠纪。以后,所有中外地质古生物学者,将东亚地区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和赫勒研究的太原标准剖面对比时,都将太原组以上的主要含煤地层,根据所含植物化石性质,几乎都置山西组于不顾而与紧覆于其上的下石盒子组相比,如朝鲜寺洞统的C-D煤组,河北开平煤田赵各庄群中部的8-10煤组。然而,太原地区的下石盒子组不含煤层。这种对比显然很勉强和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在《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一书中,我着力弄清了山西组植物群的面貌及其与下石盒子组植物群的异同关系,定其时代为早二叠世早期,据此而将朝鲜寺洞统C-D煤组所在地层和开平煤田赵各庄群8-10煤组所在地层,对比于太原地区富含可采煤层的山西组,不论从植物群的面貌,地层岩性和含煤情况来看,都是很适合的。这样一来,不只把广泛分布于华北,甚至东亚的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过去的错误对比得以改正,而且把华北的石炭、二叠纪植物群及相关地层的关系理顺了,自老而新的植物组合序列遂得以首次建立,对后续相关研究与石炭、二叠纪煤田勘探工作产生相当深远的积极作用。
我在治学方法上,除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专业、文字即中外文)、工作上的基本功外,很重视野外地质调查与室内的缜密研究相结合,在知识积累方面,很注意“博”、“约”(专、精)兼顾。我始终坚守以古、中生代植物和相关地层为主的专业园地,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有关知识的潮流走向,诸如大地构造、板块学说、古地理、动物化石、煤田地质、沉积学和新近兴起的各种生物演化学说,我都略加涉猎。创新源于积累,否则,要想在科研上有所创新突破,是不可能的。
撰稿人:李星学
点评:
李星学先生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长达60余年,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什么能取得长足进步呢?他认为:1、懂点哲学,对搞科研是大有好处的。要学会运用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综合分析的辩证思维,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2、在治学方法上,除扎实的基础知识、工作上的基本功外,很重视野外地质调查与室内的缜密研究相结合;在知识积累方面,他注意“博”、“约”(专、精)兼顾;3、寻求某个问题的解决、概念的创新乃至大的发现与发明,不能一蹴而就,而要坚忍不拔的努力,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成功喜悦。他的这些体验,对于当今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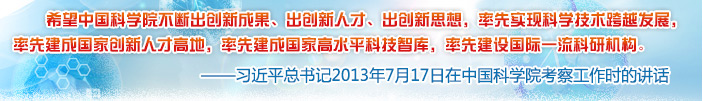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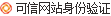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