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方华简介
李方华,著名物理学家、电子显微学家,中国单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的开创者,中国建立并发展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1932年1月出生于香港。1950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52年保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1956年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中国电子显微学会副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晶体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表面物理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固体原子像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电子衍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评定为2003年度"公众关注的10位中国科技人物"及2003年度"《中国妇女》时代人物"、中国科学院首届"十大女杰"。
相关阅读
199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欧莱雅-联合国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每年评选一次,专门授予全世界范围内卓有成就的、最杰出的科学女性,其权威性在科学界受到认可,"女科学家成就奖"也因而被称为"女性诺贝尔科学奖"。
[主持人]:
欢迎您到我们网站来。去年年初的时候,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杰出女科学家奖,当时,我们就有采访您的意思。因为您比较忙,所以就拖到现在,现在正好是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前夕,节日之前非常高兴请到您到我们网站来。在采访您之前,我们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知道您科学研究工作是很深入的,因为有好奇心,有兴趣,也有比较扎实的科学研究功底,所以在别人看来很枯燥、很寂寞的实验物理学研究工作在您看来却是很有乐趣很忙碌的一件事,请问在一步步战胜自我,持续创新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紧张和焦虑,一个人的成功是客观的因素多,还是主观的因素多。
[李方华]:
首先说枯燥,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物理学,有不少人问我,包括我们家有一些亲戚们的孩子也问我,说觉得这个物理学是很枯燥的。其实我觉得可能从事物理工作的人大家都不觉得枯燥,枯燥的原因还是因为不了解。我想了解以后就不觉得枯燥了。但是确实物理不是让一般的人都那么容易去了解,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印象。至于说有没有紧张和焦虑的那种情绪,我确实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我想一想,好像我觉得至少我没有明显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情,相反的我觉得是比较平静和坦然的。因为我们做科学研究特别是搞自然科学,主要是要认识自然界,然后让自然界的一些客观规律为我们所利用,这样我觉得我们面对的是自然界的东西,而不搀和人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究竟将来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它的。所以我不会很紧张,很焦虑,虽然有时候怕结果得不出来,但好像我也不需要去紧张焦虑,我只需要老在那儿想着,我的方案,我的策略对不对,我要不要修正,要不要改正,然后使得我的一些行为符合客观,能够得到我预想的结果。
所以我想应该是平静,我其实觉得多数情况下还是平静的,因为越平静你越容易思考,行为比较正确,你决策比较正确,然后能够得到你要的结果,我觉得坦然平静的心情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的课题都是自选的课题,没有那么大的任务,我想面对大的任务,可能会比如上天,能不能上天,大家可能等着比较着急,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做的,是大家做的,我这个工作是小组做的,所有的我都了解,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紧张和焦虑。至于您说的客观因素多还是主观因素多,我觉得主观因素应该是更重要,因为如果客观没有条件,那是什么也做不出来,但是如果有了条件以后,有了基本条件以后,我想主观上它可以创造更多条件,有些客观条件是你创造不来的,因为不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但是有些条件你可以去创造。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工作来讲,可能大家会想知道,因为我是做电子显微镜工作,显示器研究的,最重要的电子显微镜,想申请也申请不来,买也买不来,怎么办,在国内原则上可以用,但是国内上用电镜我们受一些限制。比如说拥有电镜,但操作水平有限,仪器状况不太好,我们想得到的结果得不到,我们自己派人去,很多地方不能瞎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我们就到国外去。国外他们的操作人员,特别公司的操作人员水平很高,所以我们想的,他们能够做出来。有时候我觉得人的因素应该还是更重要一些。

[主持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得物质的微观状态得以比较准确的描述,从您的经历看,在很尖端、很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人的操控性,仍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通过改变技术路线,或者改变实验方法,就能得出更好的结果,请您谈谈人与仪器设备的关系,您的科学探知过程和科学方法的归纳过程是否总是比较顺利,水到渠成,为什么?
[李方华]:
接触到仪器,我还得讲我的仪器,我是用电子显微镜的,这个电子显微镜的仪器是比较特殊一些,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精密仪器,所以不是像一般的仪器好像按着常规的按纽你就能出结果,所以操作员是非常重要的,操作员坐在那儿的时候,就必须立即判断,比如我动了这个样品,我在底下看见什么,我什么该照什么不该照,就需要做出判断。如果光是仪器在那儿,没有一个好的操作员,你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要照什么东西。所以这点我想人是一个操作仪器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仪器它的性能、指标,比如我们讲分辨率,仪器是固定了。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个水平,不一定。有的人照就照不到那个水平,有的人就能照到那个水平,就特别的熟练,操作当中需要很多调整,比如整个镜头的和轴调整,所以这些就必须有很高的水平,所以人是需要熟练操作仪器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算这个操作人员水平很高,你也能用出他的水平,你也知道该照什么,但是我们买的仪器,我们的研究工作水平未必超过国外,可能永远超不过,为什么,因为是商品仪器,全世界各地都有,你有,我有也,别人也有。如果你用它来做什么,别人也用它来做什么,所以你想靠仪器来达到一个比国际上高的水平比较难。因为我们电镜一般人的理解,你拿它来照相,照一个相发表在文章上,说明你能够看到物体里面原子的排列,这个应该是高水平的。但是你看你能做,别人也能做,所以没有新的地方。所以真正新的是靠你人去提出思想,拿这个新的思想,去用这个显微镜才能做出新的东西。当然人和仪器都有这个关系,人是活的,仪器是死的。我的思想确实和很多用户不一样,我不是把它作为简单的工具,一般拿它是做工具,我是研究电子显微学的,在国际上我们从事显微学的领域当中,大概有百分之几是从事显微镜研究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用它来做工具,这个显微学研究是干什么呢,我就研究这台设备,操作员也是最高水平的,相也照的最好,就是它了,就看见这么多东西。我能不能在照出照片之后,我能够从照片上看见东西,有用的线索存在里面,我是把它提取出来,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国外也有同样做这个工作的人,但是我不能踏着国外路子去走,别人是那么做的,我是这么做的,很多东西是立足于自己的工作去做,而不是跟着别人去做。如果别人有了思想以后,当然我也可以更完善,这也是一种工作,当然有时候也做出很好的工作。我总是喜欢提取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根本上思想和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说从顺利来讲,如果是比较顺利,新我是站得住的,因为从根上就是新的,新的思想,我请国外的最好操作员来照相,他照的相就是最好的了,但是里面有的看不清楚,不能每个原子都分开,我怎么能够把每个原子分开,我事后处理。咱们叫做时髦的词叫做离线处理,拍完之后我事后去处理,处理当中这个思想主要在这儿了,所以从这个来讲,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真正的在工作过程当中,笔直的路是没有的,总是有曲折的,一般除非我在思想错了,根本站不住,但是我们提出一个思想,决定要做的时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考虑,不会让它根上就是错的。所以往前的,曲折的路是很多的。我总是一言难尽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因为别人看见我们做的工作,或者我们做的报告,总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很顺利的,实际上只有我跟我的学生,我们了解中间的苦吃了很多,确实是各式各样的苦。也有跟人打交道的,也有跟自己的工作里面的一些实验结果打交道。
另外一点还可以说的,就是你得到国外承认顺利不顺利。这个就完全是两方面,我觉得总的情况来说,应该是顺利,因为你这个工作比较新鲜,所以一般出去以后,人家能够承认你,对你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一种评价,就是完全不承认你,对你就是否定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刚才说过,我没有沾着国外什么东西,因为从我的年龄上讲,我在国外没有一个老板,我没有跟着他走,如果跟着他走,他会很支持我,而且我给他修正一个东西,他会非常高兴,他也一定会宣传我们的工作,但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是自己的工作,一般的科学家都是比较正直的,他承认你的工作,但是有少数的人,因为你的东西做的太重要了,他也解决同一个问题,但走的不同的路,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路。我经常跟另外一些同事讲殊途同归,这个东西你比他做的好,他不高兴,他一定想办法按着你,甚至我在投我的稿子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审稿人,我的对头在审稿了,他说这样的问题已经有某某人我们都这样做了,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我当然答复他,我说科学研究是条条大路都可以走的,没有限制谁可以走一条路,但是我的文章还是接受了。最近又碰到一个审稿人很有意思,他说到21世纪了,他说你用的理论为什么不归结到某某另外一个理论上,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别人的理论,我还没答复他,我想我这个理论完全跟你有距离的,为什么归结到你那个上面去,当然我觉得是少数人这样做,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不这样做,真正的成熟的科学家也能够看得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能猜得出来谁审稿,尽管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也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方面吧。

[主持人]:
你一个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我有自己创新的地方,然后其实在获得国外的同行评价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是都那么顺利,人家觉得您顺利,实际上你是经过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然后工作的很多阶段,很多问题都已经预先设想到了,才取得了别人看起来比较顺利的结果。而在取得国际同行评价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么多的不顺。
[李方华]:
有时候尽管想到了很多问题,都设计了解决的办法,但实际上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冒出来,需要你想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做的最大熵解卷的工作,那个工作我在1991年发表第一篇文章,2004又发表了第三篇文章,这一个问题若干年之后,觉得不完善,又去解决一些问题,若干年之后还觉得有未尽之处,又来考虑这个问题,等于三篇文章才把这个问题基本上阐述清楚。
[主持人]:
50年来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后面的成果与前面的成果是否有很密切的关系,您刚才说了是三个不同阶段的三个成果才把一个问题阐述得比较清楚,你刚才讲过这个例子。
在一定的时间段,如20世纪70年代初,或者说登上一个更高的学术台阶的时候,您是否都经历过选择和把握,是如何决策的。上个世纪70年代实际上是电子显微镜技术一个发展比较快,技术上有突破的一个阶段。您在掌握比较新的技术的时候,是怎么去判断和把握的。
[李方华]:
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是文化大革命了。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是不工作的,我也一样,也没怎么工作。那个时候1973年我们所长在组织调研,他叫我负责调研我们这个学科的东西,我到图书馆一看,就看到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就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我看了以后,其实当时并不是作为选题,我作为服从所长的安排去做调研的,但是那个工作跟我的专业有一定的联系,我当时就想着,如果以后能做这个事就好了,因为这是什么东西呢?过去我们做晶体结构,比如碳原子,可以组成至少三种不同的物体,一个是煤,我们烧的煤纯粹是碳,第二是石墨,石墨现在在做仪器了,石墨干锅很有用了,这个是碳,还有金刚石,这三个完全不一样。这里面金刚石和石墨是晶体的,煤是非晶体,结构不一样,所以性能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研究晶体的结构,晶体很有用。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物质都是晶体,非晶体的比较少。研究晶体的结构,过去都是用衍射方法,X射线。电子显微学是研究到原子层次的,这个方法不是直接观察,衍射是图谱,图谱还要倒回去,这个直接一看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当时很振奋人心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激动,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不能工作了,所以调研完了以后,从1973年开始到1975年这段时间我就没停过文献,装订好的文章那么厚一本一本,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我从物理所图书馆拿回去晚上在灯下面看,整整看了两年,1971年出来了以后,我补上,一直看到1975年。所以当时我想着有朝一日如果有可能能做的话,我是非常希望做这个事。关键是它有用,我有这个基础,我觉得那个基础适合我,我当时感觉到有一些问题没解决,尽管当时发表很多文章,但是那些文章里头我觉得有些问题,好像是根本的问题没有人想到,我在里头也许能做更多的事,后来我做了很多事,所以我有这一个想法。
说到传承,我觉得我70年代想的事情是80年代才开始,而且这个工作和我前面做过的一些工作,就是在前面我大学毕业,1956年大学毕业。从1956到1957年我当时跟陆先生做X射线晶体研究,这个工作很有用的。然后1961到1965年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做了一个电子衍射,我是做的单晶体电子衍射分析,那个时候我已经独立工作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跟老师做,就自己做了,我就自己独立做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所以前面那一年加上这四五年,六年的时间应该和我后面的工作是有关的,我当时看见它,就觉得应该想办法做这个工作。其它的东西都是新的,因为那个东西是新出来的,所以都是新的。其实我没有决策权,整个的工作过去都是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变了,就是可以自选题目,这一点是一大进步。当然这个条件还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不是我决策来的,是我争取来的。首先一个争取,我当时1977年的时候,国内北京市器材公司要进口一台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虽说现在看来不怎么样了,但是那个时候它属于最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我当时就参加验收,我跟物理所的领导要求,物理所的领导支持我,然后我去了,我参加验收以后,就学着操作,跟他们关系也比较好,后来这仪器出来以后,我就争取到使用权,原来每星期能够用一天,8小时,但我把晚上利用起来,实际上我用24小时,我早晨8点进,第二天早晨8点出,基本上不睡觉,有了这个条件以后,照出一些照片,很简单的工作,拿到会议上做墙报展出的时候,日本的一位教授看到了,他是日本大阪大学的教授,他邀请我去,所以我后来就进到这个领域。另外中科院的国外设备局当时的局长是李克,他批准了在全国买两台高分辨显微镜,在物理所放一台,尽管是公用的,这是1981年底开始安装,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这么争取来的,就做下去了,一做做到现在了。
[主持人]:
实际上您面临这种把握和选择的时候,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去把握和选择的。
[主持人]:
比如说您80年代初有了自己的显微镜,在此之前,在1956年就开始跟着陆先生做了。60年代初,你又有5年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你跟踪了好几年,文献看了,盯着看了好几年,所以你才能够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了自己的仪器,然后又开始自己做自己独立的这些工作,都是一步步这样过来的。
[李方华]:
可以这样说,1956年跟陆先生那一年,以及我后面做了几年,那都是衍射的工作,是后来工作的基础工作,这个东西因为70年代才有,在国际上一报道以后,我从理论上做了准备,看了四年书,不单是文献,很多书都看了,然后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一个日本人,因为今年国际超显微学报,为我出了一本专集,序言是这个日本教授写的,他在序言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恰当的。他说我在中国文革期间,大家都不能工作的时候,他说我在那个期间学习了,还储备了新思想,他给我总结的挺好。我确实当时是这样的,因为看了东西以后有了新的想法,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我经过准备80年代到日本去了半年,到那儿实践了一下,基本的实践操作,我必须了解别人怎么工作,我才能开始我的新工作。所以我回来以后,整个实验的基础,理论的基础,自己的思想全都有了,所以一下子全都起来了,是那么长的一个积累过程。
[主持人]:
有一种积累的过程,虽然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一代人,好多后来出了大成果都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在那儿储备着,不断地积累着,然后后来科学春天来了以后又焕发出新的科研的生命力。
[李方华]:
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以后,都明白过来了,才慢慢去走,我想这个速度就慢多了。
[主持人]: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以后,有院士感言中国也有相关的工作,可惜没有进一步做下去,杨振宁先生说没有走对方向,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失误是不是偶然的呢?
[李方华]:
说实在的我对这些问题了解不多,在网上看到何祚庥院士和杨振宁院士的谈话,我觉得他们各方面都是很有功底的,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很有功底,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我来说,我是一个小人物了,而且一般我就埋头于工作,周围的事情想得比较少,我就比较专心在我工作上。所以我觉得我不敢轻易来做这个评论,确实我不敢多说了。
另外,我觉得我很理解,咱们对诺贝尔奖的问题,大家一般很愿意讨论这个事情。作为茶余饭后,我跟大家谈谈,我也愿意谈谈,这个心情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希望中国人能够赶快出一个诺贝尔奖,为中国人争光。我觉得中国人是很聪明也很能干的,究竟为什么得不出来,因素可能是很多很多的,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总结出来的,是很难的。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希望是很大的,因为国家投入明显大多了,尽管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夕阳,但已经感觉到这个好处了。所以我对年轻一代的希望是很大的。我觉得只要我们整个中国科学家在探索真理上齐心协力,一定会出来的,不管什么时候,在哪一个领域。但是我不太主张太多的在公开场合,比如报纸上多做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多讨论以后,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这个讨论有助于我们拿到诺贝尔奖,我觉得公开的讨论不一定有帮助,也许是会有一点负作用。因为说实话,诺贝尔奖是人努力做出来的,而不是讨论出来的,而且讨论也无助。因为你说讨论能帮助他往哪儿使劲,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的诺贝尔奖哪天出来了,哪天能在哪个领域,谁也说不清楚。这就要看那个领域有没有那个机遇,科学家有没有努力在那儿干,探求真理在那儿做够了,我觉得就能出来。我觉得要宣传多了,对于成熟的科学工作人员,不会有不好的影响,也许会有一点好处。但是对那些不成熟,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学生,或者是刚刚开始科研工作的,因为他还不了解究竟这个科学工作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可能会过多的去想,我今后,我要怎么去朝着诺贝尔领域去努力,这样就变成是一种负作用了。
我记得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是一个晶体学家,是我们同行。他说过一句话,他到一个小学去做报告,他第一句话说,你们别想拿诺贝尔奖,你们想拿是拿不到的,传回来就这句话,诺贝尔奖获得者,跟小学生讲,你不要去想着拿它,你只有献身科学才有可能。
[主持人]:
它是附产品。
[李方华]:
这是你的工作,然后给你的回报,你有了这个成功,自然回报会给你,这跟拿国家的其它奖是一样的。
[主持人]:
现在关于诺贝尔奖这个事报纸上有很多报道,有一个记者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实际上国内对诺贝尔奖的宣传有点过于隆重了,他说自己亲身经历了诺贝尔奖颁奖的场面,他说所有的屋子都不是那么富丽堂皇的,而且也没有专人看门,这个让进,那个不让进,就是它欢迎所有的,你只要愿意进,都可以进去。然后说的话也都非常的朴实,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天早晨在网上看见的,诺贝尔奖生物学奖,生理学奖是颁给了搞嗅觉研究的人。光明日报就去采访了咱们国内搞相关研究的耳鼻喉科的教授,问为什么搞嗅觉的会得奖,他说完全不是事先有什么预想。嗅觉是一个非常窄的领域,是替代性特别强的领域。就是因为他做了研究,关系特别大,而且带动性挺大的。谁都没想到会给嗅觉这样一个奖,所以真的不是说事先想好了,我这个东西是要报诺贝尔奖,那个东西要怎么怎么样。真的是你的科研工作做到这份上了,然后人家承认你的工作,给你的奖。您也得奖得的比较多了。去年二月份又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您曾经在获奖的时候,在巴黎得的奖,您曾经比较过女科学家成就奖和诺贝尔奖的不同,您认为它们的主要区别在哪些地方呢?
[李方华]:
也是因为当时有媒体要问我,所以我就随便说了说。这个奖确实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是女科学家奖是给女性的,诺贝尔奖不限男性,女性,尽管女性得过,但很少。而这个限制在女性,第二个不是单项成果奖。它推荐奖的材料里面就明确说明你的一项或者是一项以上的工作,是多项工作。你这个人做的所有工作,够上档次水平的,不管是几项都可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
[主持人]:
您还说过这是对于科学家一生工作的一个肯定是吗?
[李方华]:
成就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了。比如当时我的工作,从50年代我就工作,50年代的工作我没往上报,因为50年代的工作我觉得上不了那个档次,首先应该是创新性比较强的。所以我基本报的是80年代以后的工作。
[主持人]:
您如何看待个人功利和集体功利,就是现在社会人们选择是多样化的,判断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是多样化的,您觉得作为一个做科学的人动力是什么,集体功利和个人功利哪个更贴近人性的本质?
[李方华]:
做科学研究,我觉得动力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应该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动力。因为你一旦献身科学以后,你决定做科学研究,你必须有那么一个兴趣,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样的。你觉得哪个问题需要解决,那我就去解决它,首先你认识它,然后你就解决一些问题,认识它以后,因为做的都是为我们所用,比如做自然科学,物理学有很多的问题,物理学现在在近代的工业上都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一定要解决它,然后为我所用。所以首先你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如果你是搞应用的,你最后要把它搬到应用的,如果是基础的,就解决一些规律、认识的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力。
当然也可以有别的解释,比如我的动力,我要总结一些规律,总结规律也还是追求真理,没有超出追求真理。比如我要把一些东西能够用到工作上,这也还是一个追求真理。当然有的说我做科学研究是为祖国争光,这也对,你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自然是为国争光的,但是这不是最终的东西,不是必然的结果,你说中国人搞科学研究,你做到一定的档次,拿了这个奖。中国人拿了诺贝尔奖,当然是为国争光,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追求真理。
[李方华]:
再说到功利,我觉得这个应该和动力是相关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是脱开了。我觉得应该是在一起的,功利不是一个目的,你从事科学研究,功名和利益也是一个回报。个人和集体,哪一个更贴近人性的本质,比如要从一个小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说,他那个时候的人性应该是最纯的,什么外界影响都没有,我想他那时候什么也没有,但是一旦他一生下来以后,他成长,就要受环境的影响,环境有他的父母,有他的亲人,然后还要有老师,有学校,他要受到教育。尽管社会科学我懂的很少,但是我相信这个真理存在决定于意识,这个真理是绝对对的。一个人的主观意识总是受客观的存在影响形成的。现在纯粹的人性好像没有,都是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每个人就不一样,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有的人可能考虑个人比较多,有的考虑集体比较多。我们这代人从解放以后,受的集体主义教育太多了。好像总是很明白这一点,个人的利益总是在集体利益之中,总是明白的。因为到现在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都已经定形了,我觉得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已经定形了,二十多岁都已经定形了,不可能再太多的变动,这已经不容易了。这个时候人怎么去考虑问题,我觉得单位,国家的政策,科学院的政策,这个政策会左右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政策太重要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是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改动。但是有时候改动比较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出来,因为我在物理所呆了那么多年,几十年,有一些变动就很敏感,感觉得出来。因为人家也是在变动,所以感觉它一下子好像什么东西都变了,你感觉政策在变,政策导向非常明显,一个人在考虑什么,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各级领导是应该认真考虑出台的政策,出台之前它的利和弊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引导我们大家朝着集体的利益方向去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多考虑一些,为个人的利益应该在后面,我觉得这样我们的科学发展会更向前。

[网友]:
您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并在日本做过访问学者,请问你的自主创新意识是土特产还是进口的。中科院或物理所在这方面给了您何种帮助?
[李方华]:
土特产。刚才已经说了,我完全没有一点沾边,跟他们不沾边,当然我继承了在基础上面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所以我获得过一个物理学会的奖,那个奖他们评委会有一句话,也是写得比较合适的。说这个工作是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就很适合,因为这个和别的工作没有关系,也不是说没有关系,就不是把它拿过来我接着做,或者为它所发展,就是这个路子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请问李院士,中国的科技都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出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研究经费和支持,那么您在这样的科研体制下,怎样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呢?这样的科研体制能否造就一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呢?
[李方华]:
刚才有一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没回答,接着说这个正好。物理所给了我什么支持,我觉得物理所环境比较宽松,文革前后都有这个特点,比较宽松。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可以出题目,没有限制你,安排你要做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做,某一个时期,或者运动时期我是必须服从安排,但很多的时期是可以自由选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当然也有其它的支持了,没有支持你能做得出来吗?然后咱们国家一定要想国家的需求,但是作为基础研究,科学院是一样,物理所都有自己的一些选择。我也不是说我的工作整个和国家的需求没有关系,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的选题,实际上我的工作尽管是基础研究,看起来在物理学也是很窄的范围。但实际上它是为很多学科服务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我能够把晶体里面你看不清楚的原子,我能把原子一个一个看清楚,这对物理学里面的各种光电子材料,化学里面的各种材料矿物等等都需要这个东西,都是有用的。当然这个任务没下来,等于是我做了一个东西以后,别人可以拿它作为手段去用的,这个东西对国家是有用的。
[网友]:
兴趣是否可以避免浮躁,兴趣是否可以避免出现科学道德问题?
[李方华]: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兴趣和浮躁,兴趣和科学道德,这不是一个线上的问题。
[网友]:
有兴趣是不是就扎下去了。
[李方华]:
可能是好一点。浮躁和道德是有点关系,浮躁厉害了就会出现道德问题。有了兴趣以后,发生浮躁的可能性会低一些,然后科学道德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低一些,但是不能靠这个来解决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学生,甚至大学生都可以,我觉得学校从教育角度可以提高他们的兴趣。真正成为科学工作者以后,就不能靠这个了,要考虑我到底为什么要做科研,这个要求就要更高一点,不能靠说我拿兴趣来避免,这对于教育科学家是这样做的。科学道德是高层次的东西,不是光靠兴趣能解决的。如果有一些私欲,有一些想法,个人想得到什么东西,那个很强的时候,你应该想办法去克服那个,而不是光靠兴趣能够解决的。
[记者]:
您在去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您是靠哪一点打动评委的。这个奖是有十万美金作为奖金的,你是如何安排这个奖金的。这个奖对你今天的科研有没有促进,你今天的科研目标在哪里呢?
[李方华]:
第一点哪一点打动评委的。因为评委是很秘密的,评完以后也不会告诉我。我这个工作有五个推荐人,三位国内的,两位国外的。其中四位材料是我提供的,因为三位国内的人不是做电子显微镜学的,是做物理学的。包括一位国外的也是我提供,但不是我这个领域,这四位都是向我要材料,四人一个版本,我写东西不敢写得很高,我对自己比较低调的,我做了什么,我报了四项工作,这工作我不重复了,因为这四项工作,别处都有了。这项工作都是接近这个领域了。
只有一位是根本我就不知道他推荐我,是一个英国人皇家学会会员,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事后是听说那份推荐是最主要的,我想很自然因为那四份都是一样,我写的调子比较低,那份意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后来拿到的,是记者透露的,我拿到了。他也很奇怪的,因为我四项工作比较上档次。他也都提到了,每样都有评价。这位推荐人不仅是工作,他连我的工作思维方法都提到了,跟国际上对比了。我也认识他,他没告诉我,他是我们电子显微学会,当时是联合会的会长。所以他有权利,表寄给他,他就推荐了。确实我不认识他,私人没有关系,完全是工作关系。因为我当过咱们学会的理事长,主要是因为工作关系。但是国内个别人知道,他们跟我不熟悉,也没有透露这个事。国外我的个别学生也知道,但事先没有透露给我,这些人事先都讲究规矩的。事后到了巴黎以后,因为有个记者他要给我照相,这个时候才知道的。所以是哪一个打动了,我确实不清楚。
对于十万块钱怎么用,到现在为止,一分钱没用,原封不动搁在那儿了。人民币是不是要提升了,我是不是该换呢,我确实没想好怎么用这个钱。因为我去年一直生病,到底该怎么样用这个钱,用得最好,最合适,这个应该要慎重行事。
[网友]:
这个奖对您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促进,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
[李方华]:
我现在的目标,我觉得我没有更大的目标了,说实话,我没有更大的目标,因为我已经70往外了,我说我再开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很不现实了。80年代到现在做的工作,近二十年的工作我觉得还有未尽之处,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完,在我有能力做情况下,去做。说实在话二十年的工作,牵扯到前面顺利不顺利的问题了,我的经费不多,因为国家投入比较低,还有我这个领域不是很宽的领域,是很窄的领域,叫得不响的领域,所以我基本上是靠面上经费支持的。也没有招学生,所以设备很简陋,你到外边去照相,你不能专门去照,所以整个限制下,工作拖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如果经费充足的话,可能提前一半时间就可以完成了,早一点完成也许还有精力做一点别的,我首先得把这个工作做完,首先我这个工作是面向很多学科的,如果能够尽善的,别的学科可以用一下,学科应该比我开一个更新的项目更有好处。
[网友]:
您今年已经70岁的高龄,你有家庭,有子女,有丈夫,你想没想过休息,然后介绍一下您的家庭生活?
[李方华]:
家庭生活简单。真的很简单,这个简单是能说明一切的。从孩子小的时候都在家的时候,我们吃饭简单,那个时候也没法不简单,工资就那么一点,想吃好的也没钱,也买不着什么,所以就是很简单的饭。我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就是那个局面了,儿子小一点的时候,谁回家早,就谁做面条,很简单。要不食堂带一点回去,带点主食,炒一个菜,很简单,家里人很照顾我,不挑吃。穿的,你说逛商场,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合作社,上哪儿买都一样,买回来就完了。还有孩子的衣服大改小,就这么折腾,休息是没时间的,说实话除了上班八小时以外,回来还要考虑工作,还有家务,怎么办,把休息的时间挤掉,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什么剧院可以去,反正除了吃饭、睡觉,搞完家务,就看看书,是非常简单的。那个生活是年轻一代想象不到的。
[网友]:
我看的资料里面,你喜欢唱歌,是咱们科学院老干部合唱班的一员,而且您特别会做衣服,而且自己选了很多衣服款式都是很好的,包括去年颁奖的时候穿的唐装很漂亮。
[李方华]:
唱歌很喜欢唱,但是说实话工作以来一直没唱,没时间唱什么歌,再说整个工作,你有什么心情去唱歌。那个时候总理去世了,是唱了很多怀念总理的歌,但是后来这几年因为我过了65岁了,我觉得别人都说你该刹刹车了,但是我觉得刹不下来,有点问题就要做,所以就想找点事把时候占了,才参加了科学院老干部班的学习,一年就是26次,参加声乐班把时间占了,我就自己放松一下,所以就这样去了。做衣服,因为我母亲很会做衣服,她曾经靠做衣服维持生计的,我小的时候,还不需要靠这个来谋生的时候,她就觉得应该要懂点,所以给你一块布,剪个裤子,剪坏了没关系补补就行了,然后缝纫机也会踩。后来到了两个孩子需要穿衣服的时候,就用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我就给他们做,不管怎么样,就用缝纫机做出来了。至于说款式,我谈不上,我就是会缝缝补补的,但是有一连衣裙,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穿连衣裙。当时国内很少人穿,也买不到。我母亲那个时候就给我做,她给我做的连衣裙。所以后来到了文革以后,也兴穿连衣裙了,也买不到我就给我女儿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注意一下连衣裙。后来不做了,由于经济条件改善了,也不做。偶尔拿了一块布,我说做,我女儿说这样那样不满意,连衣裙后面开叉我觉得不雅观,我女儿说侧开叉也不好,所以我改了样,那是边上开叉,走路看不到腿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水平。
还有你说的唐装的问题我是生病之后,手术完了就要去巴黎,我女儿拉我上华联超市,正好春节过后,唐装减价,一试这件合适,我一看这件好就买了。有人说我是不是定做的,也不是的,我没有时间去定做,裙子是女儿的,把那个拿过来就穿了。
[网友]:
您老伴也是院士是吗?肯定互相帮助特别多吧。
[李方华]:
我们平时也忙,你说帮助反正各干各的,话也不多,吃饭才说话。
[网友]:
在物理学界女科学家很少,当初最初吸引你进入物理学界的原因是什么,这么多年碰到的困难是什么,物理上枯燥还是其它的什么呢?
[李方华]:
我上物理是上了贼船了,下不来了,我从中学就喜欢物理,这些很浅显的物理,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当时人们说物理现象怎么解释,我说物理是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是解释一些自然界的物质的本质和现象的一门学科。为什么我当时这么定义呢,因为我那时候初中高中物理,天上出彩虹了什么原因,一个石头子扔到水里面为什么会出波,就是这么浅显的,我觉得这就是物理,所以那个时候大学就念了物理学,我最早大学读的是天文系,后来转到物理系,因为我喜欢自然界的东西念了物理,后来发现物理不光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也有深奥的东西,深奥的东西也在我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现在的电视等等都有物理的因素在里面,越学就越深,这不可收拾了,进去了,了解它了,就不枯燥了,其实我学的这个东西,也许听来的人觉得是很枯燥,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但是跟我工作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喜欢上它的,只要跟我工作的人,包括我的研究生,甚至早期的一些学员,有一位学员,他来了之后,他老跟我说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一了解它以后就非常吸引他。所以我觉得现在女孩子,有时候不敢摸物理,我觉得这可能是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这个印象,觉得物理是高深莫测的,不敢做,不敢去碰它,确实应该对中学生多宣传一点,物理不是那么可怕的。我觉得没有女性不行,我觉得男性也未必就行,只要你喜欢它,你就能做。
[网友]:
李院士我是一名自然科学爱好者,我想请问您兴趣爱好与成功相距多远,我对科学怀有深厚的兴趣,要想走向成功,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李方华]:
我想兴趣当然很重要,没有兴趣谈不上,但是除了有兴趣,还得有毅力,得有毅力肯去做,你光是兴趣,那不行了。成功的过程当中没有笔直的路,必然是曲折的,这些曲折就是困难。你必须在困难面前得有毅力,你还得有自信,能够在困难面前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儿,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你去解决它,你才能够一步步往前走。当然有了兴趣已经是很好了。
[网友]:
感觉你精力充沛,对科研充满兴趣,能给我们年轻人一点启示,一点前进的动力,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现状不太满意,但又不知道如何改善,有点得过且过。
[李方华]:
其实我自己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好像没有一个信条在那儿,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特点是觉得哪有问题,哪有兴趣我就做,做了以后,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完,然后再看有什么问题再去做,我就是这么走过去的,自己好像没有明确的路要这么走。但是回过头来我得总结总结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现在很时髦的讲要寻找机会,我总结一下,我看看特别后面这些年,从80年代以后,我觉得我确实是有很多机会,这点是年轻人可能所希望要的,但机会怎么来的,机会也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机会要靠你争取。当然我今天不会讲得很多,其实我有一次大概是在北大,我拿了奖以后,后来让我在北大做报告,我在那儿讲了很多,我的机会是一环扣一环来了,有很多机会,没有上一个就没有下一个,有了这个就有下一个,机会是一环扣一环来的,所以一个人一下子不要想太多,你想我一下子争大的机会,就能够成功,这是不可能。我有机会,关键你这个人要做一件事情是有用的,对社会,对人类有用,我有兴趣,对国家有用。近的来说对我这个单位,是符合我们单位工作要求的,我就去做。做的过程中,这个洞走出去了,到了那个口,你会看见另外一个天,你又去做,机会就会很多,你做这件事情为下一个事情积累了机会,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关键你如果自己从事科学的人,你就是要追求一个真理,你肯定会成功。当然这个成功的层次不一样,你也不要希望成功一定是顶尖的人物,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不鼓励,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网友]:
你们作为院士夫妇参加体育锻炼吗?对观看比赛有兴趣吗,比如NBA什么的?
[李方华]:
我因为身体不好,被迫的,不得不锻炼一下,打打太极拳,或者散散步,也就锻炼锻炼,别的不锻炼,我老伴他是不喜欢锻炼的。
[网友]:
在你埋头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困难或困惑的时候呢?
[李方华]:
我们这代人受政治干扰比较多,我觉得那些是例外的。如果说排除政治干扰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的工作期间,工作再大的困难,我觉得不应该压倒一个人。当然工作里面的困难,你可以改变你方案、计划。比如我这个计划做不下来,我确实做不下来,条件不允许我做,我怎么办,就要改变我的计划。我做我的条件能允许我做的工作,这个也要适应客观情况。不能说遇到困难我就不做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咱们就说科研,有各种原因阻挠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计划。困难有些是条件的困难,这些困难压不垮,这些困难我可以争取条件第一,我拐了弯还可以做,没有仪器我可以到国外去做,比如人员少,人员少,我速度放慢一点,总是往前做。
我有这么一个例子,我曾经做过一项工作,这也是在我的四项工作里面,我报的三项里面的一项,后来我放弃了,原因是我觉得竞争太激烈,我并不怕竞争,但是我怕不正当的竞争,不正当的竞争,你到国外去做报告,你讲完以后,某个国家人出来以后糊里糊涂讲一阵子,我感觉我们非常新,新到他害怕你在这儿插了足,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人,后来我一衡量,还有经费的原因,等等其它的原因,我这个不做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件事情我不想说那么清楚了,就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物理所在科学院是属于那种最好的研究所之一,你又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始终在这个单位工作,是不是物理所的环境一直都是对您,就安安心心做这个工作特别有好处呢?好像每次改革都是走在前头,而且科研环境也比较好,出成果也比较多。
[李方华]:
总体上我觉得是的,从很早的时候,我觉得给我有这个感觉,当然我说要排除一些干扰的情况,你可以有自己的自由选择。但还有一点,你个人不能期望太大,你期望值太大,我觉得一个人在单位里面的时候,不要期望太多,期望太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望,你期望不太多的时候,你可能心态都是平静的。因为不可能任何事情,每一个政策对你都是适应的。
[网友]:
您现在还带学生吗?
[李方华]:
在读的有四个,都是博士生。
[网友]:
您带学生大概多少年了?
[李方华]:
我第一个学生是1981年入学的,他是77届的。
[网友]:
你现在每天还要去实验室吗?
[李方华]:
现在懒多了,每天下午去,上午就不去了。在家也不是闲着,因为反正有电脑在家里也可以做工作。
[主持人]:
非常感谢李院士到我们网站来和我们的网友交流,我们会认真体会您所告诉我们的一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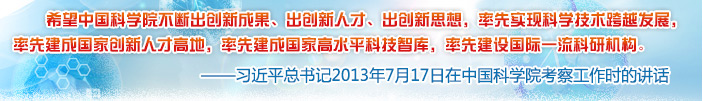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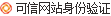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